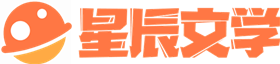接下来的几天,张诚表现得异常“安静”。
他不再像真正的小孩子那样满院子追逐鸡鸭,或是蹲在土堆边玩泥巴,而是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糊满旧报纸的土炕边,仰着小脑袋,煞有介事地盯着那些泛黄的铅字看。
母亲李秀兰起初只觉得好笑,还跟奶奶打趣:“你看这娃,装得跟个小先生似的,能看出个啥名堂来?”
但张诚的“坚持”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他不只是看,偶尔还会伸出小手指,对着某个笔画复杂的字,在空中笨拙地比划。
这天下午,奶奶去邻家串门,院子里只剩下李秀兰在纳鞋底。张诚觉得时机成熟了。
他走到母亲身边,伸出小手拽了拽她的衣角。
“妈。”
“咋了,诚娃子?”李秀兰停下手中的针线,低头看着儿子。
张诚仰起脸,努力让自己的眼神显得纯粹而渴望,用带着奶气却异常清晰的语调说:“妈,你教我认字,识数,行不?”
李秀兰愣住了。
一个四岁的农村娃,主动要求学习?这在村里几乎是闻所未闻。村里的孩子,哪个不是疯玩到七八岁,被爹妈拿着棍子撵着才肯去上学?
“你……你想学这个干啥?”李秀兰放下鞋底,把儿子拉到跟前,仔细端详着他的小脸,想从上面找出点玩笑的痕迹。但她只看到了一片认真。
张诚早就准备好了说辞。他不能表现出“生而知之”,那会被当成妖孽。他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开端”。
他指了指墙上报纸里嵌着的一幅简单的农机广告插图,上面画着个拖拉机。“那个车车,好看。旁边的字,是不是说这个车车很厉害?我想知道它说了啥。”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语气带着点孩童式的炫耀和懵懂:“我看(堂)哥的书,里面有画,还有字,我都记得住一些咧!”
他把“过目不忘”的能力,巧妙地包装成了“记性好”,并且将学习的动机归结于对陌生图案和文字的好奇。
李秀兰看着儿子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心里又是惊讶,又是难以言喻的欣喜。村里人都重视读书,谁家不希望出个文化人?儿子这么小就显出对文字的兴趣,这莫非是……开窍了?
她想起前几天儿子醒来后就有些“不一样”,更安静,眼神也更清亮。难道真是祖宗保佑,家里要出个读书的苗子?
一丝期盼在她心中悄然滋生。
“行!我娃想学,妈就教你!”李秀兰是个爽利性子,既然觉得是好事,便不再犹豫。她没读过多少书,但也上过几年小学,认些常用字,算个简单的账目还是没问题的。
她拉着张诚坐到炕沿边,就着窗外明亮的光线,指着墙上报纸最大的那个标题——“人 民 日 报”。
“来,跟妈念,‘人’。”她用粗粝的手指点着那个字。
“人。”张诚乖巧地跟着念,心里却波澜不惊。他需要的就是这个“过程”,一个让他的“学识”能够合理展现的台阶。
“这个字就是‘人’,你爹,你妈,你,都是‘人’。”李秀兰尽力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解释。
“嗯!”张诚用力点头,表现出理解了的样子。
接着,李秀兰又教了“民”和“日”,虽然解释得有些磕绊,但态度极其认真。
张诚“学”得飞快。李秀兰只教了一遍,他就能准确地指认并念出来。这让李秀兰更加惊喜。
“哎呦!我娃这脑子真好使!比你妈强多了!”她忍不住揉了揉儿子的脑袋,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随后的日子里,教张诚认字、识数,成了李秀兰劳作之余一项充满乐趣的任务。她在灶台边用烧黑的木棍在地上写“一、二、三”;在喂鸡的时候教他数“一只鸡、两只鸡”;晚上在昏黄的灯泡下,指着旧报纸上的字,一个个耐心地读给他听。
张诚则完美地扮演着一个“天赋异禀”的初学者。他控制着学习的速度,既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又不至于太过骇人听闻。他从最简单的数字和汉字开始“学起”,很快就“掌握”了百以内的数字和几十个常用字。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深处的系统界面,终于不再沉寂。
【叮!检测到宿主进行系统性识字学习,触发任务:【启蒙之路】。】
【任务要求:掌握100个常用汉字,100以内数字的认读与简单加减。】
任务已完成!!!!
【任务奖励:经验值+2(可自由分配至已解锁学科)。】
看着这个任务,张诚的嘴角在无人注意时,微微勾起一个弧度。
第一步,已经稳稳地迈出去了。
母亲李秀兰,这个勤劳质朴的农村妇女,在懵懂无知中,成为了未来学神的第一位“老师”,也为一条即将腾飞的潜龙,推开了通往知识殿堂的第一扇门。她看着儿子一天天显现出的“聪慧”,干活的劲头更足了,心里对未来的日子,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明亮期盼。
窑洞外,黄土高原的天空湛蓝如洗。窑洞里,知识的种子,正悄然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