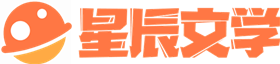周夫子的书房在书院的西南角,离教室有一段的距离,沈砚秋低着头跟在后面,青布长衫的下摆扫过门槛时带起些微尘土。
推开门,感受到的便是带着股陈旧的暖意,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雕花木窗,在青砖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空气中浮动着陈年书卷与松烟墨混合的气息。
沈砚秋垂手立在书架旁,看着夫子从紫檀木案上拿起一叠纸,那是近日学生上交的策论,最上面一卷写着他的名字。
“前儿讲《礼记》时,你答’大道之行也’那段,比前几月清明论学时通透多了。”周夫子的手指在纸页上轻轻点着,指腹因常年握笔结着薄茧,
“那时候你连’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注解都答不全,我原以为……”他顿了顿,将策论放回案上,转身时带起的风拂动了案边悬挂的竹帘,”原以为你要在那些闲言碎语里困上一阵子。”
沈砚秋沉默,不知如何回话。
目光落在案角那方端砚上。
砚池里的墨汁还泛着新鲜的光泽,是今早夫子批注课业时磨的。
他想起穿越过来的这几天,原主残留的情绪总像团湿棉絮堵在胸口。
他从记忆里看见同窗们嘲笑原主布鞋上的泥点,提起他那渔夫的父亲时语气总带着轻慢,他便索性把自己埋在自卑里,连夫子提问都低着头装聋作哑。
其实原主家庭也还可以的,能供原主读这么多年的书,还是有点家底的。
他爷爷身为金鱼村的前村长,以前他们家在村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只是在这个只是在这个看重门第与功名的世道里,金鱼村的“数一数二”到了外面,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扒拉记忆的沈砚秋不自觉的攥紧手指。
原主记忆中的周夫子从来对他不假辞色。
讲堂上抽查功课,原主答不上”三思而后行”的注解时,夫子只冷冷丢下句”朽木不可雕”;上月原主的策论写得潦草,朱笔批语更是毫不留情,”心不静则文不立,如此浮躁,枉为读书人”。
原主因此总躲着夫子走,见了那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便像见了戒尺般发怵,哪敢想有朝一日能被单独叫进书房,听夫子温言细语说这些体己话。
沈砚秋垂下眼,盯着自己布鞋上绣的防滑麻线。
这是原主娘特意加的,怕原主在书院青石地上打滑,可在那些穿锦缎靴的同窗眼里,总显得格外扎眼。
他忽然想起穿越过来那日,原主正是因为被张启元嘲笑”脚底生茧像船板”,才在神思不属,日夜焦虑最后在课堂上回答不出来被自己生生气背过去,醒来时魂儿就换成了他。
“你这几日的功课,字退步了很多”夫子忽然开口,示意他看案上摊着的两份作业。
左边是半月前原主抄写的《劝学》,虽仍显得稚嫩,却已见骨力。
右边是今天才上交的策论,通篇看下来,满纸的字东倒西歪,没个正形,别说风骨力道,就连最基本的端正都谈不上,倒像是一群没睡醒的蚂蚱,在纸上胡乱蹦跶了一通,潦草又混乱。
沈砚秋的心猛地提到嗓子眼,他知道自己的笔锋带着现代人临帖的习惯,与原主那手端正的字判若两人,难怪夫子会特意指出来。
“许是……前几日身体不适,笔力有所不够,字虚浮了,学生知错了”他低头拱手道歉。
沈砚秋低头拱手时,后颈的汗正顺着衣领往下滑,袖口下的手指绞成一团,指节抖得几乎要撞上一起。
他能感觉到夫子的目光落在那两张纸上,像春日里的细针,密密麻麻地扎在他背上。
原主的字是下过苦功的。
沈砚秋脑海里瞬间闪过原主的记忆,
天不亮就蹲在灶台前,就着灶膛的火光描红;冬日里冻裂了手,用布裹着笔杆也要写完三张纸;爷爷从镇上换来的旧拓本,被他翻得纸页发脆,边角都磨成了絮状。
那手字笔笔扎实,是苦练后才取得的成果。连村里最老的秀才都夸过“这孩子笔下有筋骨”。
可他不一样。
穿越过来才不过三天,握着毛笔的手总像生了锈,笔尖在纸上打滑,手腕的力道也拿捏不准。
原主的记忆里虽有写字的法子,可那点记忆就像隔着层薄冰的河水,看得见模样,却摸不着实在的温度。
就像在现在有很多书法大师在网上教写毛笔字,眼睛说懂了,手却不行。
毛笔字这种东西,必须花时间练,日久天长才能见效果。
他临原主的字,只得其形,不得其神。
“身体不适?”夫子拿起那页《劝学》,指尖在“锲而不舍”四字上摩挲着,“我倒记得,上月你染了风寒,趴在桌上写,字也没如今这般虚浮。”
沈砚秋的脸“腾”地红透了,连耳根都烧了起来。
原主确是如此,病中都不肯搁笔,说“一日不写,手就生了”。
那份执拗,是刻在骨子里的,他这个半路来的“借尸还魂”者,哪里学得来?
下午写在课堂上写策论时,时间短任务重,他越是想模仿原主的笔锋,手就越抖,最后写出来的字带着明显的虚浮,他自己都瞧着心虚。
“学生……学生……”他声音发抖,是心虚的表现。
夫子将两张纸并排放好,轻轻叹了口气:“你爷爷送你来时,把你练字的沙板都带来了,说你从小在上面划字,能把沙子写出‘力透沙背’的劲。”
他抬眼看向沈砚秋,目光里带着几分惋惜,“字是人的影子,藏不住偷懒,也藏不住慌张。你这字里的虚浮,不是身体不适,是手生了,心也散了。”
“要不是我能确定你沈砚秋,这字我都不敢认”
案头上的课业,新旧字迹还在无声对峙。
周夫子从案角的竹篮里抽出戒尺,对着沈砚秋命令
“伸手。”
夫子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火气。
沈砚秋慢慢摊开左手,掌心朝上。
递了过去。
那手还算不上读书人惯有的细嫩,指腹带着点乡下干活的薄茧,是原主帮爷爷修补渔网时磨的。
此刻因紧张而沁出的汗,让那些茧子显得格外分明。
周夫子的戒尺落了下来。
“啪”一声,不重,却像石子砸在水面,震得沈砚秋指尖发麻。
“第一下,记着’手熟’。”
夫子的戒尺没离开他的掌心,隔着薄薄的皮肉,能感受到竹尺的温度,”你以前每日天不亮就着灶火练字,寒冬腊月手冻裂了,裹着布条也要写满三张纸。你以前的笔力是磨出来的,不是凭空来的。”
沈砚秋的喉结滚了滚,没说话。
掌心泛起淡淡的红,那点疼倒不算什么,反让他想起昨夜临帖的光景。
原主的记忆里分明有运笔的弧度和力度,可他握笔时,手腕总像生了锈,他的字写得轻飘飘的,像根没扎根的芦苇。
戒尺又落下来,这次稍重了些。
“啪”的声响在安静的书房里荡开,惊得案头的墨碟轻轻晃了晃。
掌心的红痕深了些,热辣辣地烧起来。
“第二下,记着’心定’。”
夫子的目光落在他发颤的手腕上,”你字里的虚浮,一半是手生,一半是心不定。不要总和别人比,人越发虚浮,笔锋怎么能稳?”
这话像根细针,轻轻挑破了他心里藏着的慌。
穿越过来这几天,他总像揣着颗滚烫的石子,写字时想着”像不像”,背书时也只是听从系统的命令进行机械记忆。
“最后一下。”夫子的戒尺落下。
“记着’本分’。”
“啪”,这一下最沉,掌心瞬间红透,像落了片晚霞。
沈砚秋咬了咬下唇,没吭声,却觉得那点疼顺着胳膊往上爬,爬到心口,把那些漂浮的慌都坠了下来。
夫子收回戒尺,随手放在案上。戒尺与桌面碰撞,发出轻响。
周夫子拿起那页原主写的《劝学》,指腹抚过纸面,”今日罚你,不是罚字差,是罚你忘了’扎实’二字——不管是写字,还是做人,都得一步一个脚印,容不得半点虚浮。”
沈砚秋慢慢收回手,掌心的疼还在,却不觉得难受了。
“学生记住了。”他再次躬身,这次腰弯得很低,心服口服,诚心诚意。
“记着手熟要靠磨,心定要靠稳,更记着做人写字,都得实打实,来不得半点虚的。”
夫子看着他发红的手心,眼角的皱纹松了些,拿起墨锭往砚台里倒了点清水。
“磨墨吧。”他说,”磨完这锭墨,再写十张《论语》。然后再归家吧”
沈砚秋走到案前,慢慢研墨,墨香混着掌心的微疼漫开来,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
原来周夫子要教他的,是认识自己的不足。
窗外的蝉鸣又起,阳光落在纸上,映着他发红的手心。
磨墨的”沙沙”声里,沈砚秋忽然明白,这具身体里的魂,不管是谁,都得先学会用笨功夫,守着心里的定,才能把字写正,把路走直。
等墨磨好后。
“学生往后定当勤加练习,不负夫子教诲。”他郑重地向周夫子承诺。
周夫子“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沈砚秋拿起笔时,忽然觉得那重量沉甸甸的,不仅是一支笔的分量,更有原主幼年藏在笔墨里的光阴与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