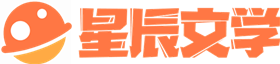简介
石语新墙这书“静之行者”写得真是超精彩超喜欢,讲述了陈三阿杰的故事,看了意犹未尽!《石语新墙》这本完结的历史古代小说已经写了132370字。
石语新墙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铁雨骑终究没能踏破凤凰城。那堵用秽土、头发丝和碎陶片夯成的“脏墙”,如同长满倒刺的荆棘丛,死死咬住了蛮族的铁蹄,为守军赢得了喘息之机。残阳如血,染红了城墙上凝固的污血和秽泥。硝烟未散,空气里弥漫着焦糊、血腥和秽土特有的、挥之不去的腥腐气味。但城还在。
活下来的人,脸上没有劫后余生的狂喜,只有麻木的疲惫和深不见底的茫然。城墙多处破损,城内的房屋更是塌了十之七八。废墟里刨出来的粮食,还不够塞满孩童的牙缝。寒冬的阴影,比蛮族的马蹄更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陈三和阿杰随着幸存的河滩镇匠人回到镇上。家,已成断壁残垣。陈三那间遮风挡雨的后院小屋,只剩半截焦黑的土墙倔强地立着,墙角的粗陶水缸碎了一地。寒风卷着雪沫,在废墟上打着旋儿。
没有欢呼,没有眼泪。人们沉默地清理着瓦砾,寻找着一切能用的东西:半截木梁,一口豁了边的铁锅,几块没烧透的砖……阿杰在倒塌的灶台灰烬里,扒拉出陈三那柄沾满秽泥、木柄烧焦一截的旧锤子。
“师傅……”阿杰把锤子递过去,声音干哑。
陈三接过锤子,用粗粝的手指抹去锤头上的泥垢,露出黝黑的铁色。他没说话,把锤子挂在了腰间半截残墙伸出的木茬上。
玉簪的冷光
霜雪冻不住凤凰城日益深重的溃烂。洪水褪去后的死寂,被一种更缓慢、更无孔不入的衰败取代。官府的赈济粥棚早已撤去,那每日一勺清可见底的稀粥,连同施粥兵卒麻木的吆喝声,都成了模糊的记忆。
废墟间,能刨出的吃食早已搜刮殆尽。饥饿,像无声的瘴气,弥漫在幸存者的窝棚里,吞噬着最后一点力气和希望。
陈三拖着那条废腿,蜷缩在偏屋的草堆里。腿伤在寒气和湿气的折磨下,日夜不休地抽痛,像有无数根冰冷的钢针在骨头缝里搅动,疼得他整夜整夜无法合眼,只能咬着破布,发出压抑的、野兽般的低哼。
阿杰跟着人去城外挖冻僵的野菜根,去结冰的河里凿洞碰运气。手冻裂了,脚冻麻了,带回来的东西却少得可怜。他看着陈三佝偻着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心里像被冰锥扎着。
襟前冷
这天傍晚,阿杰拖着冻僵的腿回来,看见陈三独自坐在断墙根下。残雪未融,夕阳的余晖给他镀上了一层凄冷的金边。陈三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正低着头,用指腹一遍遍地、极其缓慢地摩挲着。那动作不像是在抚摸,更像是在进行某种无声的告别,试图将每一丝触感都刻入骨髓。
阿杰走近几步,看清了。那是一支玉簪。通体素白,温润无瑕,只在簪头处,极其精巧地雕着两朵半开的玉兰。雕工细腻到了极致,花瓣薄如蝉翼,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落,花蕊纤毫毕现。在暮色里,簪子幽幽地散发着柔和而清冷的光泽,像一滴凝固的、永不干涸的泪。
阿杰认得这簪子。这是师娘阿暖生前最珍爱的东西,是陈三当年熬了几个通宵,用最普通的青白玉料,却倾注了全部柔情与匠心雕成的。师娘病殁那年,陈三亲手把它包在油布里,埋在了后院墙根下。 如今,它重见天日,却是在这般光景。
“师傅……”
阿杰喉咙发紧。
陈三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眼窝深陷,浑浊的眼睛里映着玉簪的冷光,也映着废墟的荒凉。他没说话,只是将玉簪紧紧攥在手心,玉簪冰凉刺骨的温度,仿佛顺着他的手臂,一直蔓延到全身,冻僵了那颗早已被苦难磨得麻木的心。
许久,他长长吁出一口白气,那气息微弱得几乎看不见,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人,得活着。”
当窗寒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雪又飘了起来。陈三揣着那支玉兰簪,带着阿杰,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百工坊。镇上的景象比河滩镇好不了多少,残垣断壁间,只有几家大户的宅院还算完整。
街角的“永通当铺”黑漆大门紧闭,檐下挂着一盏在寒风中摇晃的破旧灯笼,像一只窥视着人间苦难的冷漠眼睛。
陈三推开沉重的木门,一股阴冷潮湿、混杂着灰尘、霉烂纸张和劣质熏香的古怪气味扑面而来,瞬间包裹了他们。当铺里光线昏暗,高高的柜台像一堵冰冷的墙,隔开两个世界。
柜台后面,一个穿着臃肿棉袍、戴着铜框眼镜的老掌柜,正就着一盏油灯,慢条斯理地拨着算盘珠,发出单调的“噼啪”声,对进来的两人眼皮都未抬一下。
他那枯瘦的、正拨动着算珠的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硕大却不透光的暗绿色翡翠戒指,戒面被磨损得光滑,映着油灯,却泛不起一丝活气,只沉沉地压着指根,像一枚凝固了许久的、贪婪的眼睛。
“当什么?”
老掌柜头也不抬,声音干涩冰冷,像冻硬的石头。
陈三站在柜台下,显得格外矮小。他沉默地从怀里掏出那支玉兰簪,用掌心托着,踮起脚,轻轻放到冰冷的、沾着些许墨渍和污痕的柜台上。
玉簪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温润生光。那两朵半开的玉兰,玲珑剔透,仿佛将窗外所有的寒气与绝望都隔绝在外。
老掌柜的眼皮终于抬了一下,浑浊的眼珠透过厚厚的镜片,扫向那支簪子。他慢吞吞地放下算盘,伸出枯瘦、留着长指甲的手,拈起玉簪,举到油灯前,眯着眼细细端详。他用一个黄铜小放大镜挑剔地检视着簪身,指甲故意在玉兰花瓣边缘不易察觉的背面轻轻刮擦了一下,发出极其细微的“噌”声。
光线穿过薄薄的玉兰花瓣,映出内部极其纯净、毫无瑕疵的质地。老掌柜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精光。他慢悠悠地说:“死当?”
陈三的脊背似乎更佝偻了几分,仿佛那两个字有千斤重。他沉默着,点了点头。
“老坑和田玉,雕工也算细。”老掌柜慢悠悠地说,将玉簪放回柜台,又拿起算盘拨弄了几下,“可惜年头久了,玉色不够鲜亮,这雕花样式也过时了……兵荒马乱的,玉不当饭吃。”他拉长声调,报出一个数字。那数字低得让阿杰几乎跳起来!还不够买两斗糙米!
“掌柜的!这可是上好的和田玉!雕工多细!您再看看……”阿杰忍不住喊道,声音在空旷的当铺里显得突兀而无力。
老掌柜撩起眼皮,冷冷地瞥了阿杰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只不懂事的蝼蚁,又看向陈三:
“就这个价,不当就请回。”他作势要将玉簪推回来。
陈三一直沉默着。
柜台油灯的光晕在他脸上跳跃,映出深深的沟壑和压抑的痛苦。他攥着破旧衣襟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骨节凸起如嶙峋的山石,微微颤抖。那枚冰冷的玉簪,仿佛不仅贴着他的胸口,更压在他的心上,那是阿暖留下的最后一点温存,是他作为一个匠人所能给予的、最极致的温柔与承诺的象征。
如今,他不仅要亲手送走这份温存,更是在亲手玷污这份承诺。
阿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看着师傅,看着那支在柜台上幽幽发光的玉簪,又想起师傅夜里压抑的呻吟和空空的米瓮……
就在老掌柜的手指快要碰到玉簪时,陈三猛地伸出手,那只布满老茧、指节发白的手掌重重按在了柜台上!力道之大,震得油灯火苗都晃了晃。
“当!”
一个字,像从胸腔深处挤出的、带着血沫的石头,砸在冰冷的柜台上,也砸在阿杰心上。老掌柜似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慑住了一瞬,旋即恢复那副冰冷的模样,拉开抽屉,数出几块小小的、灰扑扑的碎银子,又拈了几串铜钱,叮叮当当地推过柜台,那声音刺耳得令人心碎。
陈三没看钱。他的目光死死盯着那支玉簪。老掌柜拿起簪子,随意地、甚至带着一丝轻蔑地丢进身后一个敞开的、堆着些许杂物的木匣里。
玉簪坠入木匣的刹那,与匣底几件不知名的旧首饰发出一声细微却清脆的碰撞。陈三鼻腔突然刺进一股陈腐的甜腥——这味道他太熟悉了,二十年前师父临终时,他从老人枕下摸出的那枚带血田黄印,就散发着同样的、属于绝望和末路的气息。
当铺梁上悬着的、早已枯黄的驱虫草束,此刻却在穿堂而过的寒风中簌簌掉落霉斑似的粉末,像是要把这典当的耻辱与冰冷彻底烙在空气里。
那粗麻当票被陈三攥出了汗,纸面上“死当不赎”的朱砂戳记正在晕开,像一滴血,慢慢染红了纸上簪头玉兰那模糊的雕纹。柜台阴影里,阿杰瞥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孩童正蹲在那里,眼睛死死盯着玉簪坠落的轨迹——三年前他娘亲的银镯也是这样滑进木匣,再没回来。
此刻那孩童鼻腔里突然涌起记忆中的奶香,那是娘亲腕上镯子贴着米汤碗的味道……那细微的、来自不同时空的绝望共鸣,像针一样扎进陈三的耳朵里。
他佝偻的背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猛地闭上眼。再睁开时,浑浊的眼里只剩下一种近乎麻木的、深不见底的平静。
他伸出颤抖的手,一把抓起柜台上的碎银和铜钱,冰冷的金属硌着他掌心的老茧,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重量,却压得他手臂直往下坠。他看也没看,转身就走,脚步有些踉跄,仿佛那支玉簪的重量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了他的腿上,他的心上。
阿杰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敞开的木匣。玉簪躺在杂物堆里,那两朵半开的玉兰,在昏暗中依旧散发着清冷的光,像一滴凝固的、再也无法流出的泪。
他追出去,风雪扑面而来,刮在脸上生疼。陈三佝偻的背影,在风雪中显得那么单薄,那么决绝。他腰间的旧锤子,随着他踉跄的步伐,一下一下,敲打着空荡荡的腰胯,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在为某种东西敲着丧钟。
寒泉种
风雪更大了。回去的路,仿佛永远走不到头。陈三攥着那几块冰冷的碎银和铜钱,指缝间仿佛还残留着玉簪最后一丝温润的触感。那不仅是妻子的遗物,更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与‘美’、与‘温柔’、与一个匠人所能守护的极致美好相连的凭证。
此刻,它变成了掌心里这几块救命的、却冰寒刺骨的金属。一场巨大的雪崩,往往始于最无声的倾斜。陈三觉得,自己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就在这当票撕下的瞬间,轰然塌陷了,并被这场大雪彻底掩埋,永不复现。
他把手一直揣在怀里,似乎想用体温焐热它们,焐热那点冰冷的希望。阿杰沉默地跟在后面,风雪迷了眼,分不清是雪水还是别的什么。
路过镇口唯一的粮店,门口排着长队,都是等着买高价粮的人,个个面黄肌瘦,眼神空洞。粮店的伙计趾高气扬,报出的粮价让阿杰倒吸一口凉气。陈三那点钱,只够买一小袋最次等的、掺着砂石和霉粒的碎米。
但‘救急的柴,湿了也得烧’。陈三没去排队。他攥着钱,径直走向粮店旁边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那里支着个小摊,摊主是个裹着破羊皮袄的干瘦老头(稷伯),守着几个不大的麻袋,里面是灰褐色、毫不起眼的、甚至带着虫眼的小颗粒旱麦种。
陈三走到摊前,没问价,只从怀里掏出所有的钱,一股脑塞进老头手里,然后指了指麻袋。
“旱麦种?”老头有些惊讶地看着陈三,撇撇嘴,声音沙哑:“老哥,脑子冻坏了吧?这点瘪种撒下去,鸟都不稀罕!不如换半袋麸皮,好歹是口嚼裹!”
陈三没说话,只把摊上仅有的两小袋旱麦种拎起,扛在肩上。麦种很轻,但压在他佝偻的背上,却仿佛有千钧之重,压得他几乎直不起腰。那是阿暖的玉簪,是他最后的体面与温存,换来的重量。
老头掂量着手里的碎银铜钱,摇摇头,没再言语,只是看着陈三佝偻扛种的身影,浑浊的眼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那眼神里既有怜悯,也有一丝同为挣扎求生者的凄楚。
陈三扛着麦种,转过身。风雪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他看着粮店门口排着长队、眼神麻木的人群,又看看自己肩上那两袋轻飘飘的、被所有人嗤笑的麦种,声音低沉,却像石头砸进冰封的河里:
“粮,吃完就没了。”
“种,埋下去,就有盼头。”
他不再理会老头,扛着麦种,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进漫天风雪里,走向那片被盐碱和死亡统治的荒地。阿杰看着师傅的背影,又看看粮店前拥挤的人群,突然明白了什么。
那两袋轻飘飘的麦种,压弯了师傅的脊梁,却在风雪深处,指向一片看不见的、渺茫却真实的绿意。那不再是关于吃饱一顿饭的挣扎,而是关于活下去的、最卑微也最宏大的赌注。
回到冰冷的窝棚,陈三没有立刻休息。他将麦种袋小心地放在干燥的角落,然后拿起那柄旧锤,拖着废腿,走到屋后那片被冰雪半掩的冻土上。他沉默地、一下一下地用锤头刨着地,刨开坚硬的冰壳,刨出下面冰冷的泥土。
他没有说话,但每一个动作都在重复着那句话:“埋下去,就有盼头。”阿杰看着,也默默拿起工具,加入了这无声的、近乎仪式般的劳作。
寒风卷着雪沫,抽打着他们,但他们刨坑的动作却异常坚定。
(第八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