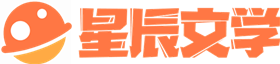简介
那十年那十年是一本让人欲罢不能的都市日常小说,作者武英殿的亮晶晶以其独特的文笔和丰富的想象力,为读者们带来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小说的主角范建勇敢、聪明、机智,深受读者们的喜爱。目前,这本小说总字数达到95927字,喜欢阅读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本精彩的小说!
那十年那十年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提起过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应该是美好的回忆吧。
在范建老家,穷归穷,但过年可不能马虎。人们忙忙碌碌干一年,还不就是为了过年这些天。人活着总得有个奔头儿。
从吃完腊八粥开始,似乎就进入了过年的节奏了。人们开始推碾子,碾大黄米,碾小黄米,碾各种需要去皮的五谷杂粮,数量多的用牲口拉,数量少的就用手推。
大黄米面碾好了,准备停当,就开始了连续几天的蒸豆包,撒年糕。
蒸豆包,撒年糕需要旺火,所以灶膛里都烧着硬木条,基本火就不断,锅上边热气腾腾,开了门,热气就会顺着门檐往外冒。
撒年糕是个技术活,火候的大小,锅里水的多少,大黄米撒到屉子上的均匀度,厚度,什么时间放芸豆,什么时间扎孔放气等等,很有讲究。
太薄了会鼓包,夹生,没法吃,太厚了,粘度不够,不筋道,还有可能个别地方不熟,所以手艺不过关的就不能伸手,否则一锅年糕就白瞎了。
撒年糕没有什么窍门,全凭感觉,但主要还是要凭经验。
范建母亲就是撒年糕的一把好手,但凡母亲能岔开活,别人家撒年糕都要请母亲去帮忙。
每逢蒸豆包,撒年糕时,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通常都是邻居几家互相帮忙,忙完你家忙我家,主妇们一边干活,一边一起聊着家长理短,平时都各忙各的,难得在一起。
每家都要蒸好多锅豆包,撒一二锅年糕,把它们放到盖帘儿上,拿到院子里,不住人的屋子里,去晾、去冻。
冬天气温低,有个一二天就冻得刚刚硬了,然后收到大缸里,盖上盖帘儿。吃的时候拿出来再放到锅里蒸一下。
各家的主妇们把平时攒的布条都掏出来,把补的不能再补的衣服用剪子铰开,然后煮小半锅面粉当浆糊,把那些碎布条粘到一块板子上。
过几天自然风干了就揭下来,放到那儿,它还有个学名叫”格褙”,人们用它纳鞋底。
纳鞋底的线叫麻线,是把一种叫芦麻的植物晾干了,用的时候把外面的那层皮剥下来,苎麻皮又长又有韧性,不易断。
然后大人小孩齐上阵,一起搓麻绳,大人把线固定住一头,小孩子把二根麻线放到一起,放到两个手心中搓转,一边搓一边后退,麻线到头了再往上续,能从炕上沿着门框搓到外屋。
小孩子们玩够了,不干了,主妇们就自己搓。她们坐在炕上,把裤腿挽上去,露出小腿,手拿上麻钱在小腿上来回搓,为了增加摩擦力,还会不时地往手心上吐些唾沫,时间久了,把小腿搓得通红。
主妇们拿出一个事先给某个人量好了的鞋样子,放到格褙上照样子剪下,一般一层厚度不够,鞋底子太薄,需要剪下三层或者四层以上,剪多少层,主要视格褙的厚度去定。
主妇们会戴上顶针,防止针尖扎到手,然后用一个带尖的锥子一层一层扎透格褙,锥子尖上有个孔,把麻线穿到孔里后,再把锥子顺着格褙拽过来,这样来来回回,细密的针脚就把几块格褙牢牢地固定在一起了。
这是个力气活,主妇们劲儿又小,干时间久了能把握锥子把儿的手心顶出血泡。
有时候主妇们便把鞋底放在一块木板子上,用锤子砸锥子把儿,锥子穿透格褙,锥子尖便扎到了木头里,这时只要把锥子拔出来,再穿上麻钱就可以了。这样就不用用手使劲顶了,虽然慢些,但是省了不少事儿。
过些时日,一双鞋底便纳好了。为了使鞋底更牢固,紧密,平整,就需要用重的东西再压鞋底一段时间,而渍酸菜的酸菜缸就派上了用场。
等过几天从酸菜缸底再拿出来,鞋底被压得又光溜又板正。
到了腊月二十左右,有养猪的人家就开始准备杀猪了。那时候没有催肥剂,就喂些谷糠,吃剩的饭菜,刷锅水之类的,夏天再喂些青菜,都是自然生长。所以喂十来个月,也就长到一百多斤。
有猪的人家杀猪时尽量错开时间,不赶在同一天,这样村里每一家,至少一家有一个人都能吃顿杀猪菜。
村里专门有一个杀猪的师傅,每一家的猪都找他杀。他有一套杀、剁、砍、吹、褪、完整的工具,活儿干得又快又干净。
把猪杀死以后,让猪四蹄朝下,趴在地桌上。这时用舀子从锅里舀出热水慢慢地,均匀地浇到猪的身上,几舀子下去,毛与皮软化了,就可以褪毛了。
杀猪师傅把毛褪到哪儿,热水就浇到哪儿,一会儿功夫,地上就堆了不少猪毛,猪鬃。
早有孩子等在那儿了,他们把地上的猪毛,猪鬃分开捡,放到两个筐里。猪鬃比猪毛贵,拿到供销社能换成小鞭炮玩。
师傅把猪开膛破肚之后,便把猪尿泡割下来扔给孩子。孩子们如获至宝,也不顾猪尿泡上全是油,用手指拽住猪尿泡口,对住嘴就使劲往里吹气,脸憋得通红,一会儿就没了力气。
然后就换人再吹,换来换去,怎么也吹不大,于是就用麻绳绑住嘴儿,把猪尿泡抛在空中,孩子们跟着猪尿泡追着,喊着,使劲用手往空中弹,不让它落地。
等到大老远就闻到煎血饼的味道时,孩子们就又都围到灶台前了。
那一大盆里红彤彤的,是猪血和荞面的混合物,里面放上佐料,搅拌均匀,是用来灌血肠的。
先把猪的大肠,小肠里面的屎倒干净,然后用筷子把肠子的里外面翻转,放到盐水里,一遍一遍地清洗,等洗干净了,再把肠子的里外面翻转过来。
在灌血肠之前,需要在锅里烙几勺血饼,尝尝咸淡。
孩子们把血饼抢光了,也得帮助大人灌血肠了。
几个人围坐在大盆前,把猪肠子套进漏斗里,用手攥紧衔接处,拿勺子舀了猪血往漏斗里放,猪血和荞面一搅拌,比较粘稠,不易往下走,不时就需要用筷子顺着漏斗往下捅一捅。
大肠好灌,又短又粗。小肠又细又长,不好灌,需要用手不停地顺着肠子往下捋,否则猪血到不了根部。
灌完了,用麻绳把头扎紧了,放锅里煮个八儿小时,就可以吃了。
而另一口锅里,早就”咕嘟咕嘟”地冒热气了,里面炖着的正是”杀猪菜”。
农村的杀猪菜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就是把猪脖子那一段肉割下来,切成小块,放到大锅里煮,等把肉煮熟了,里面再放上酸菜或者是干白菜再接着煮一段时间。
当然了,这二种菜煮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猪肠子煮熟了,杀猪菜也该出锅了,整个院子都飘着油腻腻的味道。
这时自家的孩子便会挨家挨户去喊:”吃杀猪菜啦,吃杀猪菜啦”。
于是人们就陆陆续续推开门往外走,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谁家杀猪也都一样招呼大家一起吃。
其实杀猪菜里的肉大多是肥肉片子,每个人也吃不了一二块。人们聚在一起吃这顿饭,更多的是体验这份年味儿,感受这份乡情。
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要打扫屋子,贴新窗户纸,铺新炕席,送灶王爷。
送灶王爷,就是把在供在锅台角里边的旧神龛烧了,再换个新的放那。神龛年年换,但神龛二边的对联似乎从来没变过,”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神龛前边放个盘子,盘子里边放几个带红点儿的馒头当供品,还有一个香炉,插香时用。
烧神龛时要跪在地上,嘴里念叼着,类似于祈求灶王爷,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之类的话吧。
小年一过完,就得做豆腐了。在头一天就要把黄豆用水泡上,泡不软,磨出的颗粒大,就会少出豆腐。
等泡软了就拿到小石磨跟前儿,一边转动小石磨把儿,一边往小石磨孔里放豆子,再适当往石磨孔里加些水,不一会,磨碎的豆子就呈白沫状,哗啦啦地流到石磨下的大桶里了。
等豆子磨完了,锅里的水也开了,把桶里的豆沫放到开水锅里煮,不一会锅里就起了沫子,需要用勺子把沫子打捞出来。
煮一会儿之后,看火候差不多了,就把锅里的豆汁都舀出来放到刚才那个桶里。
两个人在锅上边抻着豆腐包,另一个人把桶里的豆汁一点一点地倒到豆腐包里,分几次完成。
豆腐渣留豆腐包里了,豆浆都流到了锅里,两个人再使劲压一压,确保豆腐包里不再有豆浆了,才肯罢手。
这时,锅底加柴生火,把豆浆煮沸,把调好的卤水放入锅中,不一会,豆汁就呈鱼鳞状了,那就是豆腐脑,有爱吃的可以盛一碗。
而后,把粘稠状的豆腐汁从锅中舀出来,放到豆腐包中去沥水,水份沥得差不多了,再放到盖帘儿上压一下,卤水豆腐便做成了。
想吃冻豆腐就把豆腐切成小块放外边冻上,想吃鲜豆腐就用水泡上放在暖和的屋子里,能放好几天。
“过完小年,过大年”。北方各地过大年的习俗应该都差不多。
顺便说一嘴,范建从记事时起,母亲每年过年都会在腊月给他们四个孩子各做一件新衣服,不是裤子就是褂子。所以腊月应该是母亲最累的一个月。
新衣服只有在过年的当天,贴完对联之后才能穿上。范建穿上之后还会有些忸怩,但还是忍不住去当街转一圈,显摆一下,想让人看到,又怕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