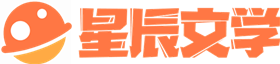简介
《明光纪事:从煤山葬父到世祖中兴》是一本让人欲罢不能的历史脑洞小说,作者“梦想成为斯总”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为读者们带来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本书的主角是朱慈烺祝朗,一个充满个性和魅力的角色。目前这本小说已经更新101257字,喜欢阅读的你快来一读为快吧!
明光纪事:从煤山葬父到世祖中兴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第一日:江锁龙蟠(1月4日)
寅时初刻,南京城尚在寒雾中沉睡,长江的波涛声隐隐传来。紫禁城内,宣宁帝朱猷榕彻夜未眠,案头堆着内阁关于“鄂毕、瑷珲惩戒营哗变士兵西线处置”与“金陵大学、松江府工人联合会联合请愿书”的奏报。
窗外,隐约能听见远处市集不安的骚动。突然,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死寂。内行厂提督曹文焕面色惨白,未经通传便闯入御书房,声音带着颤:“陛下!急报!水师…豫章舰管带温树德…反了!全舰官兵哗变,已升起叛旗,封锁下关至燕子矶江面!其余江防舰只…或被挟持,或…观望不前!”宣宁帝手中的朱笔“啪嗒”坠地,溅起几点墨痕。
他猛地站起,眼前一阵发黑,扶住御案才勉强站稳。目光下意识地瞥向暖阁方向,那里有他年幼的太子。“温树德…朕待其不薄…豫章舰…”他喃喃自语,声音干涩。封锁长江!这意味着南京已成孤城,最后的退路…断了。那撕裂夜空的、熟悉的尖啸再次灌入耳中——是1913年纪念明光北伐的汽笛!宣宁帝赤脚扑到窗边,只见漆黑的江面上,叛舰的探照灯光次第亮起,如同一条蛰伏的叛龙猛然睁开了无数只冰冷的眼睛。他颓然坐下,说道:“朕悔不听皇兄言,以至毁祖宗基业,何以见世祖?!”
第二日:孤城危旌(1月5日)
豫章舰封锁江面的消息如野火燎原。南京城内,因五四运动被镇压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因一战沙俄革命和前线明军兵变,南明与英法密约转变阵营,英法答应转交德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战后巴黎和会食言,引发了国内一片哗然。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郭钦光1919年5月1日其领导反饥饿、反贪腐、争自由、广议政的示威时被捕,因军警殴打激化肺病呕血,被送往医院伤重离世,引发五四运动)。
由京师大学堂、金陵大学学生牵头联合城内纱厂、码头工人及从西线、东线归来的伤残老兵,数万人高举着世祖朱慈烺的画像和“惩国贼、争民权、废苛政”的标语,如潮水般涌向皇城中华门。“释放被捕同窗!”“严惩军需贪腐的花袍子!”“废除《治安特别法》!”“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愤怒的声浪冲击着宫墙。
最后忠诚的禁卫军和内行厂与刑部缉捕司人员,身着靛蓝色或深灰色新式军服,手持宣宁三年式步枪,在宫门前组成单薄的人墙。枪口低垂,许多士兵的脸上写满迷茫与挣扎。他们中不少人,也曾是兴武军或定安军的一员。如今,枪口对准的,是喊着同样口号的昔日同袍和父老乡亲。
部分禁卫军士兵默默退后,拒绝举起武器。缉捕司人员则紧张地按着腰间的启新十二年式转轮手枪。宣宁帝站在宫城高处的角楼,透过琉璃窗望着宫墙外汹涌的人潮和世祖的画像,面色灰败。他身边,仅剩的几位阁臣噤若寒蝉。曹文焕低声请示是否调城外定安军入城镇压,宣宁帝疲惫地摆摆手:“罢了…再添杀戮,徒增罪孽…朕…去看看太子。”他转身走向暖阁,步履沉重。稍后,宣宁帝在议政厅召见禁卫军统领。宽阔的大厅更显空寂,唯有墙壁上明光帝身着戎装的油画目光如炬,威严地俯视着空旷的殿堂。
统领带来的并非增援计划,而是一块染血的粗麻布——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血色指印,来自百余名伤残老兵:“要活命粮,不要皇家勋章!”曹文焕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凑近低语:“陛下,江面叛舰聚集…内行厂库存尚有毒气弹…”
话音未落,随侍的史官须发皆张,厉声斥责,声音在空旷的议政厅内回荡:“陛下!此乃屠城灭国之器!陛下欲效当年建虏南下,行那屠城杀戮之暴行乎?!”宣宁帝浑身一震,目光扫过明光帝的画像,又落回那染血的请愿书,摩挲着御案上的崇祯血诏木匣,突然发出一声苦笑:“世祖爷…您当年能从豺狼环伺的北京城逃出生天,重开日月…可您的孙儿…孙儿竟连这石头城也逃不出去了!”殿内一片死寂。
第三日:裂痕深重(1月6日)
示威持续,规模不减。更令朝廷心惊的是,城内部分安防使指挥的定安军开始出现不稳迹象。一些低级军官私下议论:“惩戒营的兄弟,不也是被逼的?”“郭钦光怎么死的?军警打死的!”要求改善待遇、反对继续为“花袍子老爷”卖命的呼声在底层士兵中蔓延。内阁紧急会议争吵不休。主战派要求不惜代价,调集周边省份守备使麾下定安军入京“平乱”;主和派则哀叹大势已去,主张顺应“民意”,与示威代表谈判。宣宁帝坐在龙椅上,听着臣子们互相攻讦,只觉得头痛欲裂。
他想起了皇兄启新帝朱猷柏临终前的告诫:“德人狡诈,不可轻信。切勿受其蛊惑,贸然兴兵…贤弟需沉着稳重…切莫操之过急…”悔恨如毒蛇噬咬着他的心。他终究没能“沉着稳重”,被主战派和少壮军官勋贵子弟裹挟着加入了那场灾难性的欧陆大战,耗尽国力民力,将帝国推向了深渊。会议间隙,他匆匆回到寝宫,年幼的太子正由女官陪着读书,看见父亲,立刻扑了过来。宣宁帝紧紧抱住儿子,仿佛这是他在惊涛骇浪中唯一能抓住的浮木。宫墙之外,长江防线的堑壕里,对峙已达白热化。起义军舰炮昂首,直指皇城。
起义军阵地上,雄浑的《国际歌》声浪一波波撞击着宫墙:「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老禁卫军营长赵德昌(其祖辈随明光帝朱慈烺埋骨煤山),试图做最后的动员,他抽出佩刀指向军旗,嘶声力竭:“弟兄们!想想忠勇伯赵德运!想想我们祖辈跟随世祖爷流的血!忠义何在?!”回应他的,却是一片死寂,接着是“哐当”、“哐当”的声响——士兵们纷纷将手中的步枪扔在了冰冷的石板上。不久,一艘小船从起义军阵地驶向宫墙下,船上只有一件物品:一幅精心装裱的明光帝戎装油画像。温树德的口信随之传来:“告诉宫里人——我们反的是饿殍载道、民不聊生的朝廷,不是世祖爷打下的江山!”
第四日:暗流涌动(1月7日)
宫内的气氛压抑到极点。部分嗅觉灵敏的女官和内侍开始悄悄收拾细软。一位深受信任的三品女官(其职位由世祖废除太监后设立)冒着风险,私下求见宣宁帝,再次恳请安排太子秘密出宫避险。“陛下,事急矣!留得青山在…”宣宁帝看着依偎在自己身边,懵懂不知大祸临头的幼子,又想起煤山旧事,想起世祖背负着思宗的嘱托南奔的艰辛与决绝。他缓缓摇头,声音低沉却异常清晰:“不必了。朕…已负江山,不能再负人伦。他就在朕身边,哪里也不去。”他挥手让女官退下,将儿子搂得更紧。此举虽保全了父子之情,却也让宫中的恐慌更甚。
第五日:离心离德(1月8日)
守城禁卫军的意志进一步瓦解。一些中下层军官公开表示,除非皇帝答应与示威代表谈判,否则他们无法再向平民开枪。宫墙外,学生和工人代表在伤残老兵的护卫下,尝试与守军对话。昔日战场上同生共死的经历,此刻成了沟通的桥梁。一些士兵甚至偷偷将食物和水递给外面的学生。宣宁帝将自己关在供奉着世祖画像和崇祯血诏(那块染血的龙袍碎片)的奉先殿偏殿。他屏退左右,只带着幼子。
他让儿子安静地坐在一旁,自己则对着画像和血诏枯坐良久。他抚摸着盛放血诏的木匣,思宗皇帝(崇祯)撕心裂肺的嘱托仿佛在耳边回响:“此匣即国本!抵万军!李若琏已候崇文门秘道!走!快走!!!” 世祖完成了对思宗的承诺,而他,却要将江山断送。巨大的愧疚和无力感几乎将他压垮。他转头看向安静的儿子,孩子清澈的眼中映着烛火,也映着他这位末代帝王的无尽悲凉。
第六日:大势已去(1月9日)
城内局面彻底失控。安防使指挥的部分定安军公开倒戈,加入了示威队伍。缉捕司人员虽然装备精良,但面对汹涌的人潮和同袍的倒戈,士气彻底崩溃,或退守衙门,或干脆脱下号服混入人群。内行厂和监察院系统陷入瘫痪。内阁最后一次觐见。首辅跪地泣告:“陛下!民心尽失,军心涣散!长江锁钥已失,外无援兵可至!为保全宗庙,为南京百万生灵计…臣…泣血恳请陛下…顺应天命!”其余阁臣皆伏地不起。宣宁帝看着殿外阴沉的天色,听着远处隐隐传来的口号声,沉默了许久许久。他下意识地将手放在身边太子的头上。
最终,他极其缓慢、极其沉重地点了一下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传旨…命…温树德…入宫…议…后事。”或许是心有不甘,或许是某种仪式感驱使,宣宁帝在阁臣退下后,突然命令备车。他坚持乘坐汽车,沿着当年明光帝1660年凯旋进入北京城(后定为陪都顺天府)的象征性路线,在南京城内巡行。汽车驶过御街,窗外可见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斗争,愤怒的游行群众。街边广场上,明光帝那尊曾象征无上荣光的青铜骑马像,此刻身上被糊满了“天下为公”、“还政于民”的标语。当汽车路过旧锦衣卫衙门(现军情处)时,只见那对威严的石狮子脖颈上,赫然悬挂着一条血迹斑斑的白布,上书触目惊心的大字:“废除内行厂!”汽车行至一条偏僻小巷口,宣宁帝猛地命令停车。
他推开车门,踉跄走入巷中阴暗处,帝国的最后一丝威严在此刻彻底崩塌——他扶着冰冷的墙壁,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压抑已久的呜咽终于冲破喉咙,化作绝望的哭泣,大颗大颗的泪水混着屈辱,砸在布满污秽的地面上。巷口隐约传来乞丐嘶哑的哼唱,那曲调诡异而熟悉,歌词却令人毛骨悚然:「煤山白骨换金銮…二百七十年…又循环…」
第七日:龙驭归天(1月11日)
清晨,寒风格外凛冽。南京城在一种异样的平静中醒来。宫门缓缓打开,温树德身着笔挺的海军军官服(靛蓝色呢料,宣宁朝新式),在数名持枪水兵护卫下,昂首步入紫禁城。他没有去奉天殿,而是被直接引至宣宁帝所在的御书房。书房内,宣宁帝已换上常服,但这常服却非新制,而是一件明显带着岁月痕迹的明光朝旧式锦领暗纹龙袍,肘部一处不易察觉的破损,被精心地用金线绣补过。宣宁帝面色异常平静,只是眼神深处是无尽的疲惫与苍凉。
他端坐于御案后,年幼的太子紧紧依偎在他身侧,小手抓着父亲的衣襟,眼中充满恐惧,却强忍着没有哭出声。宣宁帝一手轻抚着儿子的后背,一手紧紧按在御案上那个静静摆放的木匣——思宗的血诏,世祖南奔的信物,南明立国的象征。目光投向走进来的温树德。“温卿…” 宣宁帝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思宗当年煤山蒙难,尚能有李若琏、王承恩忠义之士,护佑世祖爷南迁,重续国祚。可如今…朕…”他低头看了一眼身边惊恐的幼子,手臂下意识地将孩子护得更紧,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悲怆与自嘲,“竟连这石头城也护不住,连…连个托付的人都寻不出了…”
温树德肃然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而清晰:“陛下!臣温树德,以水师将士及南京父老之名起誓!必保陛下及皇室成员安全无虞,礼敬不失!新朝当以共和为体,然陛下退位,非为阶下之囚,乃顺天应人之举!”宣宁帝闻言,嘴角扯出一丝苦涩至极的笑意。他最后深深看了一眼御案上的木匣,又低头凝视着儿子惊恐却强作镇定的小脸。然后,他缓缓抬起头,对温树德,也是对这即将倾覆的帝国,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如此…便…依卿所奏。拟诏…退位吧。”
当他在退位诏书上颤抖着签下“朱猷榕”三字时,那墨迹仿佛晕染开的血泪,沉重地烙印在帝国的终章之上。是日,公历1920年1月11日,南明宣宁帝朱猷榕宣告退位,存续二百七十五年的南明王朝,正式终结。退位诏书宣读时,年幼的太子始终紧紧抓着父亲的手,未曾离开半步。这个肇始于276年前那个煤山诀别、亡命南奔之夜的不该存在的王朝,终于画上了句点。
历史宿命:朱元璋给燕王世系定的字辈为:“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前明(1368-1644)皇帝字辈用完了前两句。
南明(1645-1920)皇帝字辈用完了后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