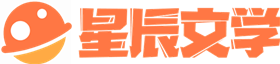简介
精选一篇种田小说《百年穿途,归乡拓富路》送给各位书友,在网上的热度非常高,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有姜砚禾,无错版非常值得期待。小说作者是鹤言笙,这个大大更新速度还不错,百年穿途,归乡拓富路目前已写102635字,小说状态连载,喜欢种田小说的书虫们快入啦~
百年穿途,归乡拓富路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摄影展的热度还没过去,县报社的专题报道又掀起了波澜。只是这次的风浪,是冲着青禾合作社来的。
那天姜砚禾正在给油菜田浇水,竹管里的清水顺着田埂漫开,润得冻土滋滋冒白烟。二柱子举着张报纸疯跑过来,报纸边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丫头,你快看!有人说咱的稻种是‘转基因怪物’!”
头版的标题用了加粗的黑字:《乡村振兴背后的隐忧 —— 青禾稻种疑为基因编辑产物》。文章里把 “定向诱变” 技术说得像洪水猛兽,还配了张青禾稻穗的特写,穗粒饱满得被批 “违背自然规律”。
“这是胡说八道!” 张寡妇正好路过,手里的洗衣盆 “哐当” 砸在石头上,肥皂水溅了满地,“咱的稻子是砚禾丫头一点点培育的,施的是农家肥,浇的是山泉水,咋就成怪物了?”
消息像长了脚,不到半天就传到了镇里。县农业局的人带着几个穿白大褂的专家来了,手里拎着采样箱,要取稻种和土壤去化验。“姜社长,有人举报你们非法使用基因编辑技术。” 为首的专家推了推眼镜,镜片在阳光下闪着冷光,“按规定,我们要进行检测。”
老李头把旱烟袋往田埂上一磕,烟锅子差点砸到采样箱:“你们凭啥查?就凭一张瞎写的报纸?” 他往专家面前凑了凑,皱纹里的泥星子差点溅到对方的白大褂上,“我种了一辈子地,就没见过这么好的稻种,你们要是敢毁了它,我跟你们拼命!”
姜砚禾拦住激动的老李头,对专家说:“可以采样,但我有个要求,检测过程要公开,结果要向村民公示。” 她转身回合作社取来一沓实验记录,“这是两年来的培育日志,从野生稻杂交到定向诱变,每一步都有记录,张教授那里还有更详细的数据。”
专家接过日志翻了翻,眉头渐渐皱起来:“定向诱变虽然不算转基因,但也属于人工干预基因表达,长期食用的安全性……”
“安全性有数据支撑。” 姜砚禾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很坚定,“我们做过三年毒理实验,小白鼠食用诱变稻种后,各项生理指标均正常,甚至比食用普通稻种的更健康。张教授的团队还做了基因测序,证明没有引入外来基因,只是激活了稻种本身的优良基因。”
她指着田埂边的野生稻:“就像野稻在自然环境中会发生变异,我们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筛选出更优良的品种。这跟袁隆平院士培育杂交水稻的原理是一样的,难道也要被质疑吗?”
这时村口传来汽车喇叭声,张教授带着省农科院的同事来了。“我听说有人在质疑定向诱变技术?” 张教授把一份厚厚的检测报告摔在桌上,“这是农业部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青禾稻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甚至优于普通稻种。”
他指着报告里的图表:“你们看,这种稻种的抗虫基因来自本地野生稻,不是外来植入的。它能抵抗稻瘟病,减少农药使用,这正是生态农业需要的。”
围观的村民里有人小声议论:“不是转基因就好,我家娃天天吃新米呢。”“就是,报纸上的话也不能全信,上次还说月牙湾的水能直接喝呢。”
县农业局的人拿着检测报告,脸色有些尴尬:“既然有权威认证,那我们就是例行检查。” 他们收起草样,临走时对姜砚禾说,“下次有新技术应用,最好提前报备,免得引起误会。”
送走专家,姜砚禾把村民们召集到青禾学院。仓库里的摄影展还没撤,月牙湾的今昔对比照就在墙上,与眼前的稻种争议形成奇妙的呼应。“大家有啥疑问,今天尽管问。” 姜砚禾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我保证知无不言。”
二柱子第一个站起来:“丫头,这定向诱变到底是啥?真的对人没啥坏处?” 他手里还攥着那张报纸,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简单说,就是用物理或化学方法,让稻种的基因发生良性突变。” 姜砚禾在黑板上画了个稻穗,旁边标上基因序列,“就像人晒太阳会变黑,是身体的自我保护,稻种也一样,我们只是帮它找到最适合生长的基因状态。”
张寡妇抱着孙子,孩子正抓着桌上的稻穗玩:“那以后还能留种不?咱农民种地,就怕种子捏在别人手里。”
“当然能留种。” 姜砚禾肯定地说,“这也是我们不用转基因的原因。咱的稻种可以自己留种、自己培育,不用依赖别人。” 她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今年留的稻种,“明年谁想种,都可以来领,不要钱。”
老李头蹲在角落里,吧嗒着旱烟袋没说话。直到大家都安静下来,他才磕了磕烟灰:“我就问一句,这稻种种出来的米,还能吃出土地的味道不?”
姜砚禾笑了:“李爷爷,您明天早上来尝尝新碾的米,保证还是那个味儿。技术是工具,关键看咋用。就像哑巴叔的相机,能拍美景,也能揭黑幕,全在咱自己咋用。”
哑巴叔突然站起来,走到墙角的相机旁,举起相机对着黑板上的稻种图拍了张照。然后他放下相机,在纸板上写:“技术无罪,滥用有罪。”
这八个字写得苍劲有力,比任何解释都管用。村民们看着纸板上的字,又看看墙上的照片,慢慢都明白了。
那天晚上,姜砚禾在日记本上写道:“技术就像水,既能灌溉良田,也能冲毁家园。关键是要有堤坝,这堤坝就是伦理和责任。” 窗外的月光洒在田埂上,油菜田在夜色里泛着淡淡的绿光,像一片安静生长的希望。
第二天一早,张寡妇端来一碗刚熬好的米粥,香气飘满了整个仓库。“尝尝,用新米熬的。” 她把碗递给姜砚禾,“我家那口子喝了都说香,比城里买的米有嚼头。”
姜砚禾舀了一勺,温热的米粥滑进喉咙,带着清甜的米香,确实是熟悉的土地味道。她知道,技术的争议不会就此消失,但只要守住本心,让技术服务于土地和人,就不怕任何质疑。
仓库外,哑巴叔正在给油菜田拍照。晨露挂在菜叶上,像一颗颗珍珠,在阳光下闪着光。他的镜头里,既有技术培育的稻种,也有自然生长的油菜,两者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存,构成了最动人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