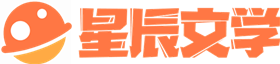第二天清晨,林晚是被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叫醒的。
她揉着眼睛打开门,看见苏漾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一把折叠梯子,额头上沁着薄汗。“早啊!我找王大爷借了梯子,他说这梯子够结实,爬阁楼没问题。”
林晚看了眼手表,才六点半。“这么早?”
“去晚了怕张奶奶担心,再说早上凉快。”苏漾晃了晃手里的包,“我带了手电筒、手套,还有……压缩饼干,万一在阁楼待久了呢。”
看着她一副要去探险的样子,林晚忍不住笑了:“只是去看看地板下面,不用这么隆重。”
“那可不一定。”苏漾神秘兮兮地眨眨眼,“说不定能找到百年前的情书呢?电报员小姐姐用莫尔斯电码写的那种。”
林晚被她逗笑了,转身回屋拿了安全帽和卷尺:“走吧,争取早点回来吃张奶奶的早饭。”
两人扛着梯子走到37号时,晨雾还没散,老巷里静悄悄的,只有早起的麻雀在槐树上叽叽喳喳地叫。苏漾熟门熟路地用钥匙打开门,一股更浓重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
“我先上去探探路。”苏漾把梯子架在阁楼入口下方,踩着梯阶往上爬,帆布包在背后晃悠,像只笨拙的小企鹅。她爬到阁楼口,回头冲林晚挥挥手,“上面空间不大,你等我先看看情况。”
林晚点点头,站在梯子下仰头看着。阁楼入口很窄,只能容一个人进出,光线从苏漾掀开的木板缝隙里漏出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哇……”苏漾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带着点惊叹,“这里面好多东西!”
“小心点,别碰掉东西。”林晚叮嘱道。
“知道啦!”苏漾应了一声,窸窸窣窣地翻找起来,“有个旧木箱,锁着的……还有几本厚厚的本子,像是台账……”
林晚等了大概十分钟,梯子突然晃动了一下,苏漾的声音带着点慌张:“林晚,你能上来搭把手吗?这箱子太重了,我搬不动。”
林晚赶紧爬上去。阁楼里果然堆满了杂物,灰尘厚得能没过脚踝,阳光从瓦片的缝隙里照进来,能看见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飞舞。苏漾蹲在一个暗红色的木箱前,正试图撬开上面的铜锁。
“别撬,找钥匙试试。”林晚从包里拿出手套戴上,翻找着旁边的杂物。旧箱子旁边堆着几本牛皮纸封面的台账,封面上写着“民国三十一年电报记录”,纸页已经脆得一碰就掉。
“找到了!”苏漾从一本旧书里翻出一把小小的铜钥匙,形状古怪,上面刻着花纹,“你看这个,是不是正好能开?”
林晚接过钥匙,插进铜锁里轻轻一转,“咔哒”一声,锁开了。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期待。
箱子里铺着一层褪色的红绸布,上面放着一个铁皮盒,几本日记,还有一个用布包着的长条形物件。苏漾小心翼翼地拿起铁皮盒,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泛黄的电报底稿,纸页上的字迹娟秀,用蓝色墨水写着密密麻麻的代码。
“这就是莫尔斯电码!”苏漾兴奋地拿起一张,“你看这个,‘A’是‘·-’,‘B’是‘-···’……我以前在书上见过!”
林晚的目光落在那几本日记上。封面是浅粉色的,上面画着一朵小小的玉兰花,字迹和电报底稿上的一样。她翻开第一页,日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六日”,字迹娟秀又带着点少女的活泼:
“今天教小漾认电码,她总把‘C’和‘K’弄混,笨得可爱。张叔说前线又打了胜仗,发报的时候手都在抖,墨水溅了一桌子……”
“小漾”?林晚抬头看向苏漾。
苏漾也看到了那句,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一定是张奶奶的姑姑!我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叫‘小漾’,后来才改了名字!”她拿起日记本,手指轻轻拂过“小漾”两个字,眼眶有点发红,“原来她说的‘教我认电码’,是真的……”
林晚继续往后翻,日记里记录着一个年轻电报员的日常:有收到捷报时的激动,有传递家信时的温柔,也有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期盼。其中一页画着一幅小小的素描,画的是37号门口的老槐树,树下站着一个穿学生装的姑娘,旁边写着:“等战争结束,想在这里开一家花店。”
“她没能等到。”苏漾的声音有些哽咽,“张奶奶说,她姑姑在民国三十三年的轰炸中去世了,当时还在发一份紧急电报。”
林晚的心情也有些沉重。她拿起那个用布包着的物件,打开一看,是一支钢笔,笔帽上刻着一朵玉兰花,笔尖有些磨损,显然用了很久。
“这应该是她的笔。”林晚把钢笔轻轻放在桌上,“这些东西……足够证明37号的历史价值了。”
苏漾用力点头,小心翼翼地把日记和电报底稿放回箱子里:“我们把这些交给文物局,他们肯定会认定这是保护建筑的!”
两人把东西重新收好,从阁楼里爬下来时,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37号的木窗棂照进来,落在地上的光斑像是跳动的音符。林晚看着手里的铁皮盒,突然觉得那些泛黄的纸页变得无比沉重——那不仅仅是历史,更是一个年轻生命留下的温度。
“先把东西放回画室吧,找个安全的地方收起来。”林晚说。
“嗯!”苏漾抱着箱子,脚步轻快得像在飞。
走到巷口时,正好遇见张奶奶拎着菜篮子回来。“丫头们,这么早去哪了?”老太太笑眯眯地问,看见苏漾怀里的箱子,“这是啥宝贝?”
“是您姑姑的东西,在阁楼里找到的。”苏漾把箱子举起来给她看,“有她的日记和电报底稿,能证明37号是保护建筑!”
张奶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接过箱子摸了又摸,眼泪掉了下来:“好孩子……终于找到了……她总说‘东西要收好,以后有人会看’,原来她早就知道……”
看着张奶奶激动的样子,林晚突然觉得,所有的坚持都值得。她拿出手机,给市文物局发了一封邮件,附上了日记和电报底稿的照片,详细说明了37号的历史。
“等文物局的认定下来,开发商就不能随便拆了。”林晚对苏漾说,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笃定。
苏漾用力点头,阳光落在她脸上,笑容比昨天的槐花糕还要甜。“我就知道,老房子不会让人失望的。”她看着林晚,眼睛亮晶晶的,“也谢谢你,林晚。如果不是你,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这些。”
林晚的心跳又开始不争气地加速。她避开苏漾的目光,看向37号的方向,阳光正好照在那栋老楼上,墙皮虽然斑驳,却透着一股倔强的生命力。
或许就像苏漾说的,有些东西,真的不会被遗忘。它们藏在阁楼的尘埃里,藏在褪色的日记里,藏在两个隔着时空却同样叫“小漾”的姑娘眼里,等着被发现,被珍惜,被好好地留在时光里。
而她和苏漾的故事,似乎也像这老巷里的晨光,正一点点变得明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