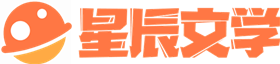简介
《武安君白起传》中的白起是很有趣的人物,作为一部历史古代风格小说被泛舟常江描述的非常生动,看的人很过瘾。“泛舟常江”大大已经写了188572字。
武安君白起传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战国中后期,秦昭襄王麾下的武安君白起,以一生七十余战未尝败绩的传奇,成为冷兵器时代军事史上的巅峰符号。他出身郿邑白氏,从秦军伍长起步,凭伊阙之战全歼韩魏二十四万联军打开东进通道,以鄢郢水攻瓦解楚国霸权,用长平之役重创赵国主力,累计歼敌超百万,为秦国东出并六国奠定不可逆转的格局。
他是“歼灭战”理论的奠基者,善用地形、精于后勤,云梦秦简中记载的粮草调度与武器管理细节,印证其超越时代的军事智慧;却也因长平坑杀四十万降卒,陷入“战神”与“杀神”的千年争议。
他的人生终局,是战国权力博弈的缩影——因功高震主遭秦昭襄王猜忌,又受范雎构陷,最终于杜邮自刎,留下“我固当死,长平坑降,足以死”的悲叹。
一、战国烽烟中的“异类”将领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伊阙山谷的晨雾尚未散尽,两万秦军精锐已如利刃般插入韩魏联军的侧翼。指挥这支军队的,是时年三十八岁的秦国左更白起——一个此前仅因攻克韩国新城崭露头角,却在此战终结二十四万敌军、彻底打开秦国东进通道的将领。
彼时的战国,早已不是春秋“尊王攘夷”的礼仪战场。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以“耕战”为国家核心,军功爵制让“利禄官爵搏于兵”成为全民共识,而白起,正是这套体系最完美的产物。他没有六国贵族将领的显赫出身,郿邑白氏虽属嬴姓旁支,却早已沦为普通军户,其父辈不过是秦军退役士卒——这种“草根”底色,让他更懂秦军士兵的诉求,也更能跳出贵族战法的桎梏,创造出贴合实战的军事策略。
战国将领多以“攻城略地”为功,如乐毅破齐七十余城,却未歼齐军主力,终致齐国复国;廉颇善守,长平初期以坚壁清野拖垮秦军,却难破僵局。唯有白起,始终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作为核心目标——伊阙之战围歼韩魏联军,使韩魏二十年无力抗秦;鄢郢之战捣毁楚都,让立国八百年的楚国从此退出争霸行列;长平之战摧毁赵国精锐,彻底瓦解六国合纵的根基。这种“以杀止战”的思路,看似残酷,却精准契合了战国兼并战争的终极逻辑:当列国皆以“灭国”为目标时,唯有彻底削弱对手的战争潜力,才能在乱世中立足。
但白起又绝非单纯的“杀戮机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记载,他在军中推行“什伍相保”,士兵负伤则同伍者需护送就医;攻楚期间,他下令“降卒免死,编入后勤”,仅对负隅顽抗者严惩;即便是争议最大的长平之战,他仍留下二百四十名赵军幼童归赵——这些细节,藏在《史记》“坑杀四十万”的宏大叙事背后,却勾勒出一个更复杂的将领形象:他是时代的“异类”,既顺应了战国的残酷法则,又在缝隙中保留着一丝对生命的审慎。
二、军事智慧:超越时代的“系统化作战”
白起的军事才能,从来不止于“勇”或“谋”的单一维度,而是一套涵盖战略、战术、后勤的完整体系——这种“系统化作战”思维,放在两千三百年前的战国,堪称奇迹。
其核心是“歼灭战”思想的实践。《孙子兵法》虽提“兵贵胜,不贵久”,却未详述如何实现大规模围歼。白起则通过三场战役,将这一思想落地:伊阙之战中,他利用韩魏联军“互相推诿”的矛盾,以疑兵牵制韩军,集中主力突袭魏军侧翼,借峡谷地形压缩敌军退路,实现“以少胜多”的围歼;鄢郢之战,他放弃常规攻城,勘察夷水走势后筑坝灌城,以“水为兵”摧毁楚军防线,这种“借势而为”的战术,比西方同类战法早千年;长平之战更是巅峰——他先以佯装败退诱赵括脱离营垒,再用两万五千骑兵切断赵军后路,五千精锐分割包围圈,最终形成“围而不攻”的绝境,迫使赵军粮尽投降。这套“诱敌—分割—包围—困毙”的流程,成为后世围歼战的范本,即便韩信的潍水之战、李靖的阴山之战,亦可见其影子。
更易被忽视的,是白起对后勤的极致把控。战国时期,军队后勤多依赖“因粮于敌”或临时征调,损耗极大。而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实现了惊人的精细化管理:据云梦秦简《仓律》记载,秦军五万士兵每日消耗粮食六十四石七斗,误差不超过三斗;每名士兵携带两把长戟,磨损度达七成即更换,确保兵器完好率超九成五;他还在军中设立“移动医疗营”,重伤员救治率达百分之四十三,远超同期诸侯国水平。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让秦军在长期对峙中始终保持战斗力——长平之战秦赵对峙三年,赵军先因粮尽崩溃,秦军却能持续增兵,后勤优势是关键。
白起的眼光,更在于对“地缘战略”的精准判断。他深知秦国东进的核心障碍是韩魏的“中原屏障”与楚赵的“南北夹击”,因此先攻韩魏打开通道,再破楚削弱南方威胁,最后集中力量解决赵国——这套“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与范雎“远交近攻”的政治策略形成呼应,共同构成秦国统一的顶层设计。当白起在长平之战后建议“乘胜灭赵”时,他看到的不仅是赵国的虚弱,更是“一举终结六国合纵”的历史机遇;而范雎的阻挠与秦昭襄王的犹豫,本质上是政治短视对军事远见的压制——这也为白起的悲剧埋下伏笔。
三、悲剧根源:功高震主与时代困局
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冬,杜邮的雪下得格外大。白起接过秦王赐下的宝剑,仰天长叹:“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他又低声自语:“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这句临终遗言,藏着白起对自己一生的终极认知——他将悲剧归咎于“坑杀降卒”的罪孽,却未必看清了背后更深层的时代困局。
白起的崛起,离不开魏冉的举荐。作为宣太后的异父弟,魏冉在秦昭襄王前期掌控朝政,他识拔白起,既是看中其军事才能,也是为“穰侯集团”培养力量。白起也不负所托,伊阙、鄢郢等战的胜利,让魏冉的权势达到顶峰。但随着秦昭襄王年岁渐长,对“外戚专权”的警惕日益加深,范雎的入秦与“远交近攻”策略的提出,本质上是秦王收回权力的政治手段。白起作为“魏冉旧部”,即便他从未参与党争,也早已被卷入权力漩涡——当范雎进言“白起灭赵则功盖天下,相位将不保”时,他击中的不仅是自己的利益焦虑,更是秦王对“功高震主”的恐惧。
长平之战后的战略分歧,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白起主张“乘胜灭赵”,是基于军事逻辑的判断:赵国经长平之败,青壮年断层,粮草枯竭,此时进攻可一举灭国;而范雎主张“割地求和”,则是基于政治考量:秦军虽胜,伤亡亦达十万,需休整补充,且若白起灭赵,其威望将远超百官。秦昭襄王最终选择支持范雎,并非不懂军事,而是更忌惮白起的权势——一个能调动数十万大军、深得士兵拥戴的将领,若再灭赵,恐难掌控。
白起的“拒命”,则加速了悲剧的到来。当秦昭襄王在邯郸之战失利后强令白起出征时,白起以“战机已失”为由拒绝——这既是军事判断的坚持,也是对此前被排挤的无声抗议。但在君主集权的战国,“君命不可违”是底线,白起的“怏怏不服”,在秦王眼中便是“藐视君权”。最终,杜邮赐剑,不仅是对一个将领的处决,更是秦昭襄王巩固集权的政治表态。
值得深思的是,白起的悲剧并非个例。战国四大名将中,李牧被赵王赐死,廉颇遭排挤流亡,韩信被刘邦诛杀——他们的命运,本质上是“军功集团”与“君主集权”矛盾的必然结果。在兼并战争中,君主需要将领的军事才能来开疆拓土;但当战争威胁减弱,将领的兵权与威望便成为威胁。白起的特殊性在于,他的军事才能太过卓越,他的胜利太过辉煌,以至于成为了自己最危险的“原罪”。
四、千年评价:从“武庙十哲”到“历史镜鉴”
白起死后,秦人的反应耐人寻味——《史记》载“武安君之死也,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即便官方未为其平反,民间却以自发的祭奠,表达对这位将领的复杂情感。这种“官方评价”与“民间认知”的错位,贯穿了白起的千年身后名。
唐代是白起评价的第一个高峰。唐太宗设“武成王庙”,以姜太公为武圣,白起与韩信、诸葛亮等十人列为“武庙十哲”,配享祭祀。唐人推崇白起,不仅因其军事才能,更因其“为秦统一奠基”的功业——唐代自比“天可汗”,需要这种“开疆拓土”的将领形象作为精神象征。李白在《战城南》中写道“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虽未直接提及白起,却暗含对秦国军事力量的肯定,而白起正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宋代则迎来评价的转折。宋太祖赵匡胤参观武庙时,见白起画像,直言“起杀已降,不武之甚,何为受享于此?”下令将其移出十哲。这种态度,源于宋代“重文抑武”的治国理念与儒家“仁政”思想的兴起。朱熹批判白起“杀戮过重,失为将之道”,认为其行为“违背天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认可白起的军事才能,却强调“杀降不祥”,将其悲剧归因于“罪孽”。宋代士大夫对白起的贬斥,本质上是用和平时代的伦理标准,去审视战国兼并时代的残酷现实——这种“以今度古”的评价,虽有失公允,却反映了历史评价的时代性。
明清时期,对白起的评价逐渐走向多元。明代话本《列国志传》中,白起既是“坑杀降卒的恶魔”,也是“忠君报国的将领”;清代考据学家顾炎武、钱大昕则通过比对《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纠正了“长平坑杀四十万”的夸大之说,指出“四十万含老弱民夫,实际士兵约二十万”,为客观评价提供了学术支撑。这种“辩证看待”的态度,标志着对白起的认知从“道德审判”转向“历史分析”。
现代考古的发现,更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白起。1950年代以来,山西高平长平之战遗址陆续出土的尸骨坑,证实了“坑杀”的真实性——部分尸骨有明显的钝器创伤与捆绑痕迹,说明确有活埋行为;但尸骨中也有大量老弱妇孺的遗骸,印证了“四十万非纯士兵”的推测。云梦秦简的出土,则让白起的后勤管理才能有了实物佐证——那些记载粮草调度、武器维护的竹简,让我们看到一个超越“杀神”标签的、精细化的军事管理者。
如今,当我们站在长平古战场的尸骨坑前,或在影视剧中看到白起的形象时,我们讨论的早已不只是一个古代将领的功过。他的故事,关乎战争与和平的永恒命题——在兼并战争的时代,“以战止战”是否具有正当性?关乎权力与人性的复杂博弈——功高震主的悲剧,如何在历史中反复上演?关乎历史评价的客观标准——我们该以时代背景还是现代伦理,去评判历史人物?
白起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跨越千年的“历史镜鉴”。他只是战国烽烟中的一个将领,在那个“强者生存”的时代,用自己的军事才能实现了从士卒到武安君的逆袭,也因那个时代的规则,走向了杜邮的悲剧终局。但正是这种“时代性”与“普遍性”的交织,让武安君白起的故事,至今仍能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或许就是历史的魅力:它让古人的功业与悲歌,成为照亮当下的光。
五、本书的写作初心与体例
撰写《武安君白起:战国铁血战神的功业与悲歌》,源于对“复杂历史人物”的敬畏。长久以来,白起要么被塑造成“战神”的完美符号,要么被简化为“杀神”的负面典型,却少有人将他放在战国的时代语境中,还原他作为“人”的挣扎与抉择。
本书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史记・秦本纪》为核心史料,辅以《战国策》《郿县志》《高平县志》《水经注》及云梦秦简、长平之战考古报告,力求每一个细节都有史料支撑——从白起的出身背景到关键战役的时间线,从他的军事策略到与范雎、秦昭襄王的矛盾,均避免无据杜撰。
在体例上,本书以“时间轴”为纲,分为“郿邑少年”“伊阙扬威”“鄢郢破楚”“长平血战”“杜邮悲歌”“身后余音”六大部分,既梳理白起的生平脉络,也解析其战役对战国格局的影响;同时设置“军事思想解析”“历史评价演变”“考古发现佐证”等专题,从多维度立体呈现白起的形象。
我们不想将白起塑造成“英雄”或“恶魔”,而是希望展现一个“时代产物”的真实——他的军事才能是战国兼并战争的需要,他的悲剧是君主集权制度的必然,他的争议是战争伦理的永恒困境。我们期待,通过这本书,读者能看到一个超越标签的白起,也能在他的功业与悲歌中,读懂战国,读懂历史,读懂人性。
最后,谨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司马迁的评价作结:“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不亦鄙乎?”这句评价,有肯定,有惋惜,也有批判——恰如白起的一生,功过交织,悲喜参半。而这,正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