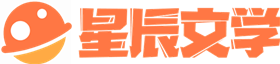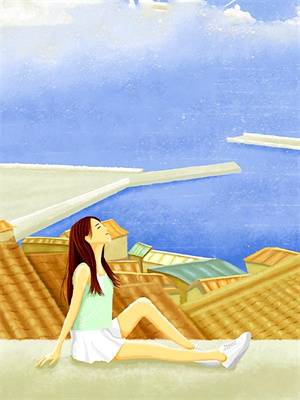简介
最近非常热门的一本传统玄幻小说,楼兰英雄诀,已经吸引了大量书迷的关注。小说的主角阿吉木大祭司以其独特的个性和魅力,让读者们深深着迷。作者道法之自然以其细腻的笔触,将故事描绘得生动有趣,让人欲罢不能。
楼兰英雄诀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之一
公元前177年的仲春,罗布泊的晨雾还没散尽,阿吉木已经提着皮囊,踩着湿软的盐碱地往芦苇荡深处走。十五岁的少年,小腿上绑着磨得发亮的羚羊皮护腿,裸露的胳膊晒成了古铜色,唯有一双眼睛,像刚从湖面捞起的晨露,亮得能映出远处的雪山。
“阿吉木!等等我!”身后传来清脆的喊声,是同部落的少女阿依娜,她怀里抱着一捆刚割下的芦苇,芦苇叶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发梢,“首领让你回来就去议事帐,说今天要分新打来的黄羊!”
阿吉木停下脚步,回头冲她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知道了,等我给‘老伙计’打够水就回。”他说的“老伙计”,是部落里那匹瘸了腿的老马,去年冬天跟着父亲去焉耆草原换粮,被风沙卷倒的胡杨砸伤了后腿,从此只能留在营地附近,由阿吉木照看着。
罗布泊的清晨是安静的,只有芦苇被风吹动的“沙沙”声,还有水鸟掠过湖面时的轻啼。雾气慢慢散开,湖面像一块巨大的碧玉,映着远处连绵的阿尔金山,山顶的积雪在晨光里泛着淡金色的光。阿吉木蹲下身,用皮囊舀水,指尖触到湖水的瞬间,一阵凉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心口——他从小就听部落里的老人说,罗布泊是水神的居所,湖水会随着水神的心情涨落,要是得罪了水神,整片绿洲都会变成黄沙。
他舀满皮囊,刚要起身,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不是部落里那种慢悠悠的踱步,而是带着一股狠劲的奔袭。阿吉木心里一紧,猛地站起身,往马蹄声来的方向望去。雾气还没完全消散,只能看到远处的沙丘后面,扬起了一道长长的黄尘,像一条扭动的黄龙,正朝着营地的方向扑来。
“是骑兵!”阿吉木脱口而出,心脏“咚咚”地跳起来。部落里的男人都知道,这几年匈奴的骑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罗布泊周边,他们抢粮食、抢牛羊,有时候还会掳走部落里的女人和孩子。去年冬天,隔壁的若羌部落就被匈奴人洗劫过,据说整个部落的帐篷都被烧了,尸体扔在雪地里,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块。
阿依娜也慌了,手里的芦苇掉在地上,声音发颤:“怎么办?要不要去告诉首领?”
“你快跑,去议事帐报信!”阿吉木把皮囊往腰间一拴,抽出腰间的短刀——那是父亲给他的成人礼,刀身是用西域特产的镔铁打造的,虽然不长,却异常锋利,“我去看看情况,别让他们靠近营地!”
阿依娜还想说什么,阿吉木已经像羚羊一样蹿了出去,顺着芦苇荡的边缘,朝着黄尘扬起的方向跑去。他知道,营地就在罗布泊西岸的绿洲上,要是匈奴人直接冲过去,部落里的老人和孩子根本来不及躲。他得想办法拖延一点时间,哪怕只有片刻。
跑了没多远,雾气彻底散了,阿吉木终于看清了来者的模样。大约三十多个匈奴骑兵,个个穿着黑色的皮甲,头上戴着插着羽毛的头盔,手里握着长矛,胯下的战马嘶鸣着,每一次蹄子落地,都像是在敲打着大地的心脏。他们的脸上带着狞笑,眼睛里闪着贪婪的光,显然是把这片绿洲当成了囊中之物。
阿吉木屏住呼吸,躲在一丛粗壮的芦苇后面,看着骑兵们越来越近。他注意到,为首的那个匈奴人,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从额头一直划到下巴,看起来格外狰狞。那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勒住马绳,朝着阿吉木藏身的方向大喝一声:“出来!藏头露尾的小东西!”
阿吉木知道自己藏不住了,他握紧短刀,慢慢从芦苇丛里走出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这里是楼兰人的地盘,你们不该来。”
刀疤脸匈奴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像破锣一样难听:“楼兰人?不过是一群靠水吃饭的蝼蚁!今天爷爷来,是给你们送‘福气’的——把粮食和牛羊都交出来,再选十个漂亮的女人,或许能饶你们一命!”
他身后的骑兵们也跟着哄笑,有人还故意用长矛刺向旁边的芦苇,芦苇秆断裂的声音,在阿吉木听来格外刺耳。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却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些骑兵的对手。部落里的青壮大多出去打猎了,留在营地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几个看守帐篷的族人,就算全部加起来,也打不过这三十多个装备精良的匈奴兵。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阿吉木回头一看,是父亲和几个族人赶来了。父亲是楼兰部落的首领,名叫昆莫,今年四十多岁,脸上刻着风霜的痕迹,眼神却依旧锐利。他看到阿吉木站在匈奴人面前,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快步走到儿子身边,把他护在身后。
“你们是匈奴哪个部落的?”昆莫盯着刀疤脸,声音低沉,“罗布泊周边的部落,都和你们的单于有过约定,互不侵扰,你们为何违约?”
刀疤脸嗤笑一声:“约定?那是给听话的人看的!如今冒顿单于一统草原,西域这些小部落,都该乖乖给大匈奴进贡!别废话,赶紧把东西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们血洗你们的营地!”
昆莫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知道匈奴人的凶残,也知道自己现在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他们。但他是部落的首领,要是真的把粮食和女人交出去,部落以后就再也抬不起头,只会成为匈奴人随意宰割的羔羊。
“我们没有那么多粮食,”昆莫缓缓说道,“今年冬天雪大,牲畜死了不少,族人都快吃不饱了,只能给你们凑出十只羊,至于女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坚定,“楼兰的女人,是用来养育孩子、守护家园的,不是给人当玩物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刀疤脸勃然大怒,猛地举起长矛,“给我冲!把他们的帐篷烧了,女人和孩子都带走!”
匈奴骑兵们立刻催动战马,朝着昆莫等人冲过来。昆莫大喊一声:“族人,拿起武器,保护营地!”他身后的几个族人立刻抽出弯刀,和阿吉木一起,挡在了匈奴人的面前。
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就这样在罗布泊的岸边爆发了。阿吉木握着短刀,跟着父亲冲了上去。他看到一个匈奴骑兵挥舞着长矛,朝着父亲刺来,他想也没想,就扑了过去,用尽全力把父亲推开。长矛擦着他的肩膀划过去,带走了一片皮肉,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服。
“阿吉木!”昆莫惊呼一声,挥刀砍向那个匈奴骑兵,刀身砍在对方的皮甲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却没能造成致命伤。
匈奴骑兵人多势众,又骑着马,楼兰人只能靠双脚在盐碱地上奔跑,很快就落了下风。阿吉木看到一个族人被战马撞倒,接着被匈奴人的长矛刺穿了胸膛,鲜血喷在地上,很快就被盐碱地吸了进去,只留下一片暗红色的印记。他还看到阿依娜的父亲,那个平时总爱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老人,为了保护怀里的孩子,被刀疤脸一刀砍中了脖子,老人倒在地上,眼睛还圆睁着,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死了。
阿吉木的眼睛红了,他像一头愤怒的小兽,朝着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匈奴骑兵冲过去。那个骑兵没想到这个半大的孩子会这么凶猛,一时没防备,被阿吉木一刀划中了马腿。战马吃痛,猛地扬起前蹄,把骑兵甩了下来。阿吉木趁机扑上去,用短刀朝着骑兵的胸口刺去,却被对方用长矛挡住了。两人扭打在一起,阿吉木年纪小,力气不如对方,很快就被按在了地上。骑兵狞笑着,举起弯刀,就要朝着他的脑袋砍下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更密集的马蹄声,还夹杂着一阵奇怪的呼喊声。阿吉木抬头一看,只见沙丘后面又冲出来一群人,大约二十多个,个个骑着马,手里拿着弓箭,身上穿着和楼兰人不一样的衣服——他们是隔壁的且末部落的人!
且末部落和楼兰部落向来不和,因为争夺罗布泊边缘的一块草地,两个部落已经争斗了好几年。阿吉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他们竟然会来帮忙。
刀疤脸显然也愣住了,他没想到会突然冒出一群且末人,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且末部落的首领是个络腮胡子的大汉,他朝着昆莫大喊:“昆莫,我们不是来帮你的,只是匈奴人抢了你的,下次就会抢我们的!今天暂且联手,把这些杂碎赶出去!”
昆莫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声回应:“好!今天过后,罗布泊的草地,我们两个部落平分!”
有了且末人的加入,局势瞬间逆转。且末人擅长射箭,他们骑着马,在匈奴人周围游走,一箭接着一箭,很快就射倒了几个匈奴骑兵。刀疤脸一看情况不对,知道再打下去讨不到好,狠狠瞪了昆莫一眼,大喊一声:“撤!”
匈奴骑兵们立刻调转马头,朝着来路狂奔而去,临走前,还放了一把火,把楼兰人靠近湖边的几顶帐篷烧了。火焰冲天,浓烟滚滚,映得罗布泊的湖面都变成了暗红色。
之二
匈奴人走后,营地一片狼藉。烧焦的帐篷残骸散落在地上,几个族人的尸体躺在血泊里,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此起彼伏。阿吉木坐在地上,肩膀上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来。
阿依娜蹲在父亲的尸体旁边,哭得撕心裂肺。阿吉木走过去,想安慰她几句,却发现自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能默默地帮她,把老人的尸体抬到营地后面的沙地上,和其他牺牲的族人放在一起。
昆莫正在和且末部落的首领商量事情,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阿吉木走过去的时候,正好听到络腮胡子大汉说:“匈奴人这次没占到便宜,下次肯定会带更多人来。我们且末部落人少,经不起折腾,以后不会再管你们的事了。”
昆莫叹了口气:“我知道,今天多谢你们了。答应你们的草地,我会让族人划出来。”
络腮胡子摆了摆手,带着自己的人转身离开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昆莫的眼神变得格外沉重。他回头看到阿吉木,招了招手:“你过来。”
阿吉木走到父亲面前,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知道,今天自己冲动地冲上去,差点送了命,父亲肯定会生气。
出乎意料的是,昆莫没有骂他,只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手指触到他肩膀上的伤口时,动作明显顿了一下:“疼吗?”
阿吉木摇了摇头:“不疼。”
“说谎,”昆莫笑了笑,眼里却没有一丝笑意,“伤口流了那么多血,怎么会不疼。今天你很勇敢,但也很鲁莽。要是你死了,我怎么向你母亲交代?”
提到母亲,阿吉木的鼻子一酸。他的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瘟疫去世了,这些年,父亲又当爹又当妈,把他拉扯大。他知道父亲不容易,也知道自己今天确实太冲动了。
“父亲,我错了。”阿吉木低声说。
昆莫叹了口气,拉着他走到湖边,指着眼前的罗布泊:“你看这湖水,看起来平静,可一旦起了风沙,就能把岸边的一切都卷走。我们楼兰人,就像这湖边的芦苇,看起来长得茂盛,可风一吹,就容易折断。”他顿了顿,眼神望向远处的雪山,“匈奴人太强了,我们和且末部落加起来,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今天他们走了,明天还会来,后天可能会带更多的人来。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们的部落就会像被风沙卷走的芦苇一样,消失在这片沙海里。”
阿吉木看着父亲,第一次发现他的头发里已经有了白丝。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今天的战斗,已经让部落损失惨重,要是匈奴人真的再来,他们可能真的抵挡不住。
“那我们该怎么办?”阿吉木忍不住问,“难道真的要把粮食和女人交给他们吗?”
“当然不能,”昆莫的眼神变得坚定,“我们楼兰人,就算死,也不能做别人的奴隶。可是,光靠勇敢是不够的,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尊严。”他低头看着阿吉木,“你今天冲上去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阿吉木想了想,说:“我想保护营地,想保护阿依娜,想保护部落里的人。我不想看到他们像阿依娜的父亲一样,死在匈奴人的刀下。”
昆莫点了点头:“很好,你有一颗守护的心。可是,守护不是光靠刀就能做到的。你看那些商队,他们从东方来,带着丝绸和铁器,要去西方换玉石和香料。他们没有多少武器,却能安全地穿过这片沙海,你知道为什么吗?”
阿吉木摇了摇头。他见过商队,每年春天和秋天,都会有商队从罗布泊岸边经过,他们会在营地附近停留,用丝绸换一些楼兰人的皮毛和干果。那些商人看起来文质彬彬,不像能打仗的样子,可确实很少听说他们被匈奴人抢劫。
“因为他们有城池,”昆莫说,“在东方,有一个叫‘汉’的大国,他们的人都住在高大的城池里,城墙又高又厚,匈奴人就算再厉害,也很难攻破。商队走到哪里,只要进了城池,就能得到保护。”
“城池?”阿吉木愣住了,他只听说过城池,却从来没见过。部落里的老人说,城池是用石头和泥土砌成的,比最高的胡杨还要高,站在城墙上,能看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
“对,城池,”昆莫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如果我们也能像汉人一样,在这片绿洲上建起一座城池,把族人都聚集在里面,再修上高大的城墙,匈奴人的骑兵就算来了,也很难攻进来。到时候,我们就能守住我们的粮食,守住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守住我们的家园。”
阿吉木的心跳突然加速了。他想象着一座高大的城池,矗立在罗布泊岸边,城墙像雪山一样坚固,族人在城里安居乐业,再也不用害怕匈奴人的骑兵。这个想法像一颗种子,突然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可是,我们能建成城池吗?”阿吉木有些不确定,“我们从来没有建过城池,而且,部落里的人都习惯了游牧,他们愿意住在城里吗?”
“会的,”昆莫肯定地说,“没有人愿意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要他们知道,住在城里能安全,能活下去,就会愿意的。而且,我们楼兰的位置很好,东边是阳关,西边是尼雅,南边是阿尔金山,北边是哈密,正好在商队走的两条路中间。如果我们建起城池,让商队在城里休息、交易,他们就会给我们带来丝绸、铁器,还有我们需要的粮食。到时候,我们不仅能活下去,还能活得比现在好。”
阿吉木看着父亲,突然觉得他的身影变得格外高大。他想起今天匈奴人嚣张的嘴脸,想起阿依娜父亲死去的模样,想起那些被烧焦的帐篷。他握紧了拳头,心里的那颗种子,仿佛在一瞬间就发了芽。
“父亲,我想和你一起建城,”阿吉木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坚定,“我想让楼兰人,再也不用害怕匈奴人的刀,再也不用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在面前。”
昆莫看着儿子,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伸手拍了拍阿吉木的肩膀,虽然碰到了伤口,阿吉木却没有皱一下眉头。
“好,”昆莫说,“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学习怎么和族人商量,怎么和商队打交道,怎么把一座城池,从这片沙地里建起来。这会很难,可能需要很多年,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可能会流血牺牲。你怕吗?”
“我不怕,”阿吉木说,声音虽然还带着少年的稚嫩,却异常坚定,“只要能让部落活下去,我什么都不怕。”
夕阳慢慢落到了雪山后面,把罗布泊的湖面染成了一片金红色。昆莫和阿吉木站在湖边,身影被拉得很长。远处,族人已经开始清理营地的残骸,妇女们的哭声渐渐停了下来,孩子们在帐篷旁边,好奇地看着这一切。
阿吉木知道,从今天起,他的人生会和以前不一样。他不再只是首领的儿子,不再只是一个会用刀的少年。他要和父亲一起,为楼兰人建造一座城池,一座能守护家园的城池。他不知道这条路会有多难,但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走下去,因为他是楼兰人,是罗布泊水神的孩子!
之三
夜幕像一块厚重的黑丝绒,缓缓覆盖住罗布泊。营地中央燃起了篝火,火焰跳动着,将周围族人的脸庞映得忽明忽暗。昆莫让族人把牺牲者的尸体用麻布裹好,放在篝火旁,准备明天清晨按照部落的习俗,将他们安葬在靠近雪山的沙坡上——那里是楼兰人心中离“天神”最近的地方,能让逝者的灵魂顺着雪水,回到生命最初的源头。
阿吉木坐在篝火边,肩膀上的伤口已经被族里的老巫医用草药包扎好,草药带着一股苦涩的清香,却压不住皮肉撕裂的隐痛。他手里拿着一块烤得半熟的黄羊肉,却没什么胃口,目光一直落在篝火对面的阿依娜身上。
阿依娜低着头,用一根小木棍拨弄着篝火,火光映在她脸上,能看到未干的泪痕。她的父亲是部落里最擅长鞣制皮革的人,阿吉木小时候穿的第一双羊皮靴,就是她父亲亲手做的,靴筒上还绣着小小的芦苇花纹。可现在,那个总是笑着摸他头的老人,变成了裹在麻布下的冰冷躯体。
阿吉木站起身,拿着手里的黄羊肉走过去,在阿依娜身边坐下,把肉递到她面前:“吃点吧,明天还要帮着安葬你父亲,没力气不行。”
阿依娜抬起头,眼睛红肿得像两颗熟透的沙棘果,她摇了摇头,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我吃不下去。”她顿了顿,突然抓住阿吉木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阿吉木,匈奴人还会来吗?下次他们来,我们是不是都会死?”
阿吉木看着她恐惧的眼神,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他想起白天父亲说的“建城”的话,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却还是用力点了点头,语气尽量坚定:“不会的。我和父亲要建一座城池,很高很大的城池,匈奴人的骑兵冲不进来,我们都会好好活着。”
“城池?”阿依娜愣住了,眼里闪过一丝茫然,“就是老人故事里,汉人住的那种用石头堆起来的东西吗?”
“是,”阿吉木说,努力回忆着父亲描述的样子,“比咱们最高的胡杨树还高,墙比野牛的身子还厚,站在城墙上,能看到几十里外的匈奴人。以后我们住在里面,再也不用怕他们烧帐篷、杀人了。”
阿依娜的眼睛里慢慢泛起了光,却又很快黯淡下去:“可是……我们从来没建过城池,族里的人都习惯了跟着水草走,他们会愿意住在城里吗?而且,建城要很多石头吧?咱们这里只有沙子和芦苇。”
阿吉木被问住了。他只想着建城能保护大家,却没想过这些具体的问题。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不知道,但我父亲说能成,就一定能成。他是部落的首领,从来没骗过我们。”
就在这时,昆莫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陶碗,碗里盛着清澈的湖水。他听到了两个孩子的对话,在阿吉木身边坐下,把陶碗递给阿依娜:“喝口水吧,罗布泊的水,能让心定下来。”
阿依娜接过陶碗,小口抿了一口,冰凉的湖水滑过喉咙,让她纷乱的心绪稍微平静了些。昆莫看着篝火旁沉默的族人,声音不高,却能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楚:“今天,我们失去了三位族人,他们是为了保护部落、保护家园死的,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
族人纷纷抬起头,目光落在昆莫身上,有悲伤,有恐惧,还有一丝茫然——每个人都在担心,匈奴人下次来的时候,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裹在麻布下的人。
昆莫继续说道:“匈奴人的骑兵比我们强,比且末人强,靠一时的联手,只能挡得住一次,挡不住一辈子。想要活下去,想要不被人欺负,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属于楼兰人的路。”他顿了顿,伸手指了指远处的罗布泊,“这片湖,是水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它让我们在沙海里活了下来;但光靠湖水不够,我们还要给自己造一个‘壳’,一个能挡住刀箭、挡住风沙的壳。”
“首领,您说的‘壳’,就是城池吗?”一个年长的族人开口问道,他叫巴图,是部落里最有威望的氏族长老之一,脸上刻满了皱纹,眼神却很清明。
“是,”昆莫点了点头,“我想在湖边的高地上建一座城,把所有族人都聚在里面,用夯土和芦苇杆筑墙,用胡杨木做城门。商队来了,能在城里歇脚、交易,我们能换他们的铁器、粮食;匈奴人来了,我们能躲在城里,用弓箭守住城墙。这样,我们不用再跟着水草迁徙,不用再担心帐篷被烧,孩子们能在安全的地方长大,老人们能安安稳稳地晒太阳。”
巴图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首领,这太冒险了。我们楼兰人世代游牧,哪里有水,哪里有草,我们就去哪里。建了城,就像把脚绑在了沙子上,要是湖水干了,或者风沙把城埋了,我们连逃的地方都没有。”
其他族人也纷纷附和,有人说:“是啊,汉人会建城,可我们不会,万一建到一半,匈奴人来了,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人说:“夯土和芦苇杆能挡住骑兵吗?匈奴人的长矛,一下子就能戳破吧?”
质疑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来,阿吉木看着父亲,心里有些着急,想站起来反驳,却被昆莫按住了肩膀。昆莫脸上没有丝毫慌乱,等族人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才缓缓说道:“巴图长老说得对,建城有风险,可我们现在这样,就没有风险吗?今天匈奴人来了,我们靠且末人帮忙才躲过一劫,下次呢?且末人不会每次都来,等他们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他站起身,走到篝火边,捡起一根燃烧的木棍,指着营地周围:“你们看,我们的帐篷搭在平地上,匈奴人的骑兵一来,不用费力就能冲进来;我们的粮食放在皮囊里,他们一抢就能抢走;我们的孩子、女人,在马蹄下像羔羊一样脆弱。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过多久?”
木棍上的火星掉落在沙地上,很快熄灭了。昆莫的声音带着一种沉重的力量,让每个族人都低下了头。是啊,今天的战斗,已经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脆弱,像巴图这样的老人,更是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恐惧,只是从来没有人像昆莫这样,把“改变”的想法摆到所有人面前。
昆莫继续说道:“我知道大家怕,怕建城失败,怕失去现在的生活。但我向你们保证,建城之前,我们会先派人去东边看看,看看汉人是怎么建城的,看看他们的城墙是怎么挡住骑兵的;我们会和商队打交道,用我们的皮毛、玉石,换他们的铁器、工具;我们会找最好的地方,选在湖水不会干涸、风沙吹不到的高地上。”
他把目光投向巴图,语气带着尊敬:“巴图长老,您走过的地方最多,见过的商队也最多,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下次商队来的时候,问问他们,汉人建城用什么法子,需要什么东西?”
巴图看着昆莫,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首领,我信你。只是……建城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得慢慢商量,让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干。”
“好!”昆莫笑了,“从明天起,我们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议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担心,都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
族人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有人开始小声讨论建城的事,有人问商队什么时候会来,还有人说自己会编芦苇席,可以用来铺城墙。篝火旁的气氛,从悲伤和恐惧,慢慢变成了一种带着忐忑的期待。阿吉木看着这一切,心里松了口气,他知道,父亲已经迈出了最难的一步——让族人愿意相信“建城”这个听起来遥不可及的想法。
深夜,篝火渐渐小了下去,族人大多回帐篷休息了。阿吉木跟着父亲回到他们的议事帐,帐篷里铺着一张很大的羊皮地图,上面用炭笔勾勒出罗布泊的轮廓,还有周边部落的位置。昆莫蹲在地图前,用手指在湖边的一片高地上画了个圈:“这里,就是我想建城的地方。”
阿吉木凑过去看,那片高地在罗布泊的西岸,比周围的平地高出两丈多,东边靠着湖水,西边是一片茂密的胡杨林,既能挡住西边来的风沙,又能方便取水。他点了点头:“这里好,站在上面,能看到很远的地方。”
“嗯,”昆莫说,“而且这里的土是胶土,和芦苇杆混在一起夯筑,能变得很结实,比普通的沙子耐用。”他抬头看着阿吉木,“明天开始,你跟着巴图长老,去湖边看看,哪些地方的胶土多,哪些地方的芦苇长得粗壮,记下来,以后建城用得上。”
“好!”阿吉木用力点头,心里充满了干劲,仿佛伤口的疼痛都减轻了不少。
昆莫看着儿子,突然叹了口气:“阿吉木,你今天很勇敢,但以后不能再像今天那样冲动了。你是首领的儿子,以后要做部落的守护者,守护者不是要第一个冲上去拼命,而是要学会怎么让更多人活下来。”
阿吉木低下头:“我知道了,父亲。今天要不是且末人来了,我可能已经死了,还会连累你。”
“知道就好,”昆莫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以后遇到事,先想想怎么才能保住更多人,而不是只想着自己不怕死。勇敢是好事,但只有勇敢,没有脑子,是保护不了任何人的。”
阿吉木抬起头,看着父亲的眼睛,认真地点了点头。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今天自己冲上去的时候,只想着不能让匈奴人欺负部落,却没想过自己万一死了,会让父亲伤心,会让部落失去首领的继承人。从今天起,他要学着像父亲一样,用脑子思考,而不是只用刀说话。
之四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阿吉木就跟着巴图长老出发了。巴图长老已经六十多岁了,背有点驼,却精神矍铄,手里拿着一根用胡杨木做的拐杖,走路比年轻人还稳。两人沿着罗布泊的湖边走,巴图长老一边走,一边教阿吉木辨认土地:“你看,这种土,用手一捏能成团,松开手又能慢慢散开,就是胶土,用来筑墙最好;要是一捏就碎,就是沙土,没用。”
阿吉木蹲下身,抓起一把土,按照巴图长老说的试了试,果然能捏成团,松开手后,土团慢慢散开,留下一道清晰的手印。他兴奋地说:“长老,这里的胶土好多啊,够我们建城墙了!”
巴图长老笑了笑:“傻孩子,建一座城,需要的胶土可不是一点点。我们得把湖边所有的胶土地都标出来,还要看看哪些地方的土最结实。”
两人继续往前走,走到一片芦苇荡前,巴图长老停下脚步,指着芦苇说:“你看这些芦苇,长得又高又粗,杆子里的纤维结实,用来混在胶土里,能让城墙更不容易开裂。我们得选那些长了三年以上的芦苇,年轻的芦苇太嫩,没用。”
阿吉木看着芦苇荡,密密麻麻的芦苇长得比他还高,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像一首轻柔的歌。他想起昨天阿依娜怀里抱着的芦苇,大概就是从这里割的。他问巴图长老:“长老,我们要割多少芦苇才够啊?”
“最少要割上千捆,”巴图长老说,“而且得在秋天之前割完,秋天的芦苇杆最结实。现在才仲春,还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准备。”
两人在湖边走了一整天,把有胶土的地方、芦苇茂密的地方,都用石头做了标记。中午的时候,他们在芦苇荡里找了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巴图长老从皮囊里拿出几块干饼,递给阿吉木一块:“吃吧,这是用胡麻籽和玉米面做的,顶饿。”
阿吉木接过干饼,咬了一口,有点粗糙,却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他一边吃,一边问巴图长老:“长老,你见过汉人建的城吗?是什么样子的?”
巴图长老喝了口水,慢慢说道:“二十多年前,我跟着你爷爷去东边的阳关附近换粮,见过汉人的城。那城墙,比咱们部落里最高的胡杨树还高,全是用大石块和夯土筑成的,城门是用厚厚的胡杨木做的,上面还包着铁皮,关起来的时候,几十个人都推不动。城里有街道,有房子,还有专门给商队歇脚的地方,可热闹了。”
阿吉木听得眼睛发亮:“那城里的人,是不是不用怕匈奴人了?”
“是啊,”巴图长老点了点头,“匈奴人很少去攻汉人的城,因为根本攻不下来。他们的城墙上,有很多射箭的口子,汉人站在里面,能射到城外的人,城外的人却很难射到他们。”
阿吉木心里暗暗记下,想着等下次议事的时候,把这些告诉父亲,说不定能用到建城上。他又问:“长老,商队一般什么时候来啊?我们什么时候能问他们建城的事?”
“快了,”巴图长老说,“每年三月,都会有中原的商队从阳关过来,沿着罗布泊走,去西边的焉耆、龟兹换玉石。最多再过十天,他们就该到了。”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中原的商队,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建城的办法,阿吉木心里充满了期待。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沙子:“长老,我们继续走吧,争取今天把南边的湖边都看完。”
巴图长老笑着点了点头:“好,看来你是真的想建城了。”
两人继续往南走,太阳渐渐升到了头顶,晒得沙子发烫,脚下的盐碱地反射着刺眼的光。阿吉木的额头渗出了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沙子上,很快就消失了。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心里像揣着一团火,烧得他浑身是劲。
走到下午的时候,两人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争吵声。巴图长老皱了皱眉:“好像是咱们部落的人和且末人在吵架,走,去看看。”
阿吉木跟着巴图长老快步走过去,只见在一片靠近草地的湖边,几个楼兰部落的族人正和几个且末人争得面红耳赤。一个楼兰族人手里拿着一把断了的镰刀,大声喊道:“这片草地是我们先发现的,你们凭什么来割草?”
一个且末人也不甘示弱:“沙地里的草,是水神给所有人的,凭什么只能你们割?再说,昨天我们还帮你们打匈奴人,割点草怎么了?”
原来,昨天昆莫答应且末人,要把罗布泊边缘的草地平分,可今天两边的族人来割草的时候,却因为草地的边界吵了起来。阿吉木知道,这片草地是部落里牲畜春天主要的草料来源,要是被且末人占了,部落里的牛羊可能会不够吃。
巴图长老走上前,大声说道:“都别吵了!昨天首领说了,草地平分,我们现在就划一条线,线这边归楼兰,线那边归且末,谁也不能越线,怎么样?”
楼兰人和且末人互相看了看,都点了点头。巴图长老让阿吉木找来一根长木棍,在草地上划了一条直线,直线沿着湖边的芦苇丛,把草地分成了两半,正好在两边族人都能接受的位置。
划完线,巴图长老对两边的人说:“大家都是靠罗布泊吃饭的,昨天还一起打匈奴人,要是因为这点草吵起来,让匈奴人看了笑话,值得吗?以后大家各守各的边界,互相帮忙,才能在沙海里活下去。”
两边的族人都低下了头,不再争吵,各自拿起镰刀,在自己的那片草地上割起草来。阿吉木看着这一幕,心里突然明白了父亲昨天说的话——楼兰人单打独斗,赢不了匈奴人;和且末人闹矛盾,也只会让大家都活不好。想要活下去,不仅要建城,还要和周围的部落好好相处,互相帮忙。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阿吉木和巴图长老终于看完了南边的湖边,回到了营地。昆莫正在帐篷里等着他们,看到两人回来,立刻迎了上去:“怎么样?有没有找到合适的胶土和芦苇?”
阿吉木把今天标记的地方一一告诉父亲,还把巴图长老描述的汉人城池的样子说了出来。昆莫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一下头,眼里露出满意的神色:“好,做得很好。明天,我们就把族人分成几队,一队去挖胶土,一队去割芦苇,一队去胡杨林里砍木材,先把建城的材料准备起来。”
“父亲,商队还有十天左右就到了,巴图长老说,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建城的法子。”阿吉木说。
“嗯,”昆莫点了点头,手指在羊皮地图上轻轻敲击着,“等商队来了,我亲自去和他们谈。不仅要问建城的法子,还要和他们换些铁器——挖胶土、夯土墙,没有铁锨、铁夯可不行,总不能一直用石斧、木槌硬扛。”
阿吉木看着父亲指尖下的地图,突然想起下午和且末人争执草地的事,连忙说道:“父亲,今天我和巴图长老遇到楼兰人和且末人抢草地,差点吵起来。巴图长老划了线,才把事情解决。我觉得,以后我们建了城,是不是也该和且末人、若羌人这些周边部落好好商量,大家别再为了一点水、一点草争斗,万一匈奴人再来,还能像昨天那样联手对抗?”
昆莫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伸手拍了拍阿吉木的肩膀:“你能想到这一层,比只想着用刀拼杀强多了。楼兰夹在匈奴和中原之间,又处在丝路要道上,光靠自己的城墙挡不住所有风雨。和周边部落交好,就像给城池多筑了一道‘外墙’,这才是长久活下去的道理。等忙完建城的准备,我就去拜访且末部落的首领,把草地划分的事彻底定下来,再约着若羌部落的人见一面,大家喝一碗酒,把过去的恩怨先放一放。”
父子俩正说着,帐篷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巴图长老掀开门帘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块用油布包着的东西:“首领,你看看这个。”他把油布展开,里面是一块巴掌大的黑色石头,表面光滑,用手一摸,还带着一丝凉意。
“这是……”昆莫拿起石头,放在鼻尖闻了闻,没有异味,“从哪里找到的?”
“下午在南边湖边的沙地里捡的,”巴图长老说,“我看这石头比普通石头硬,用刀划都划不出痕迹,说不定能用来做筑墙的工具,或者铺在城门下面,耐磨。”
阿吉木也凑过去看,伸手摸了摸那块黑石,确实坚硬无比。他想起巴图长老说过,汉人城池的城门包着铁皮,要是用这种黑石铺城门地基,说不定比普通沙土结实得多。他刚想开口,昆莫已经把石头递给了他:“你拿着,明天找个石匠,试试能不能把它打成小块,要是能用,就多派人去南边湖边找找,越多越好。”
“好!”阿吉木小心翼翼地把黑石包好,揣进怀里,仿佛揣着一件宝贝。
第二天一早,营地就热闹了起来。昆莫按照计划,把族人分成了三队:青壮男子跟着巴图长老去挖胶土,妇女们带着孩子们去割芦苇,经验丰富的老匠人则跟着阿吉木去胡杨林砍木材。阿吉木肩上的伤口还没好利索,却执意要去胡杨林——砍木材需要选粗壮、笔直的胡杨,还要用石斧一点点凿断,是个力气活,他想多帮衬着点。
胡杨林离营地有两里地,走进林子,密密麻麻的胡杨树遮天蔽日,树干粗壮得要两三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树皮裂开深深的纹路,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老匠人领头走到一棵枯死的胡杨前,拍了拍树干:“就从枯树开始砍,活树要留着,不然来年风沙来了,连个挡的都没有。”
阿吉木点点头,拿起一把石斧,学着老匠人的样子,对准树干底部的纹路砍下去。石斧的刃口不算锋利,砍在硬邦邦的胡杨木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震得他手臂发麻。老匠人看他吃力,笑着说:“别急,砍树要找纹路顺的地方,一下下慢慢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阿吉木按照老匠人说的,调整了姿势,对准树干的纹路,一下又一下地凿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点,胡杨林里只有“咚咚”的凿木声,还有风吹过树叶的“哗哗”声。不知不觉间,他的额头渗出了汗水,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衣服也被汗水浸湿,贴在背上,伤口处传来一阵阵刺痛。但他咬着牙,没喊一声累——他想起父亲说的“守护者要让更多人活下来”,这点痛,和族人面临的危险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中午的时候,妇女们背着割好的芦苇路过胡杨林,阿依娜也在其中。她看到阿吉木挥着石斧,脸上满是汗水,连忙放下背上的芦苇捆,跑过去递给他一个水囊:“歇会儿吧,喝口水。”
阿吉木停下手里的活,接过水囊,猛灌了几口。冰凉的湖水滑过喉咙,瞬间驱散了不少疲惫。他看着阿依娜背上的芦苇捆,比昨天看到的粗壮了不少,笑着说:“你们割的芦苇真结实,用来筑墙肯定好用。”
阿依娜脸颊微红,低下头说:“长老说,要选长了三年以上的芦苇,我们都挑着粗的割。对了,营地那边挖胶土很顺利,巴图长老说,今天就能挖够筑一段城墙的土了。”
“太好了!”阿吉木眼睛一亮,“等我们砍够木材,就能先试着筑一段矮墙,看看用胶土和芦苇混在一起,到底结实不结实。”
阿依娜点了点头,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用胡麻籽做的饼,塞到阿吉木手里:“这是我娘做的,你吃点,补充力气。”说完,她怕被别人看到,红着脸转身跑回了队伍里,跟着其他妇女一起,背着芦苇捆往营地走去。
阿吉木拿着手里的胡麻饼,看着阿依娜的背影,心里暖暖的。他咬了一口饼,香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仿佛连手臂的酸痛都减轻了不少。老匠人在一旁看得清楚,笑着打趣道:“阿吉木,阿依娜这丫头对你可是上心得很,以后建好了城,可得风风光光地把她娶进门。”
阿吉木的脸一下子红了,连忙低下头,拿起石斧继续凿树,嘴里含糊地说:“长老别取笑我了,我们还小呢。”
老匠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胡杨林里回荡。周围的族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原本沉闷的劳作,因为这小小的插曲,变得轻松了不少。
接下来的几天,楼兰部落的人都在忙着准备建城的材料。挖胶土的队伍在湖边挖出了一条条深沟,胶土被装在皮囊里,一趟趟运回营地;割芦苇的妇女和孩子们把芦苇捆成大捆,在营地旁边堆成了一座小山;砍木材的队伍也运回了不少粗壮的胡杨木,老匠人正带着人,用石斧把木材削成整齐的木柱——这些木柱要用来做城墙的骨架,把胶土和芦苇固定住。
阿吉木每天都跟着队伍忙碌,白天要么在胡杨林砍树,要么帮着老匠人处理木材,晚上则跟着父亲和巴图长老一起议事,商量建城的细节。他肩上的伤口慢慢愈合了,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像一条小小的蛇,爬在他的肩膀上。他不觉得丑,反而觉得这道疤痕是一种纪念——纪念那些为了部落牺牲的族人,也纪念自己第一次真正懂得“守护”的意义。
这天傍晚,阿吉木正跟着老匠人给木柱打磨边缘,突然看到营地门口传来一阵骚动。他抬头一看,只见几个穿着中原服饰的人,牵着几匹骆驼,正朝着议事帐的方向走去。骆驼背上驮着鼓鼓囊囊的包袱,不用问,肯定是商队到了。
阿吉木心里一阵激动,扔下手里的砂纸,拔腿就往议事帐跑。他跑到帐外时,昆莫已经迎了上去,正和商队的领头人说话。那领头人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一身蓝色的丝绸长袍,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说话的声音不高,却很有底气。
“这位就是楼兰部落的昆莫首领吧?”领头人拱了拱手,操着不太流利的西域话说道,“在下张远,是从长安来的商队首领,路过贵地,想借个地方歇脚,顺便和首领换些皮毛、玉石,不知首领是否愿意?”
昆莫也拱了拱手,笑着说:“张首领客气了,楼兰欢迎你们。商队的人可以在营地旁边搭帐篷,骆驼也能喂些草料。至于交换物资,我们正有此意,只是我还有件事想请教张首领,不知可否借一步说话?”
张远点了点头:“首领请讲。”
昆莫把张远请进议事帐,阿吉木想跟着进去,却被昆莫拦住了:“你去让厨房准备些吃的,招待商队的人,我和张首领谈完事情就出来。”
阿吉木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听话地转身去了厨房。他找到负责做饭的族人,让他们杀一只羊,再煮些粟米饭——他听巴图长老说,中原人喜欢吃米饭,不像西域人,顿顿离不开肉和奶。
等他安排好饭菜,回到议事帐外时,帐门已经掀开了,昆莫和张远正笑着走出来。看两人的表情,谈话应该很顺利。阿吉木连忙迎上去,昆莫拍了拍他的肩膀,对张远说:“张首领,这是我的儿子阿吉木,以后建城的事,他也会帮忙,有什么不懂的,还请张首领多指点。”
张远看向阿吉木,笑着点了点头:“阿吉木小兄弟看着很精神,是个能干事的人。建城可不是小事,需要的不仅是力气,还有法子。我已经和昆莫首领说好了,明天我让商队的工匠,给你们讲讲中原筑墙的法子,还能把我们多余的几把铁锨、铁夯送给你们,算是一点心意。”
阿吉木又惊又喜,连忙向张远道谢:“多谢张首领!”
张远笑了笑:“不用客气,我们商队走南闯北,靠的就是和各个部落交好。你们建了城,以后我们路过这里,也能有个安稳的歇脚地方,算是互相帮忙。”
当天晚上,营地中央的篝火比往常更旺了。楼兰人杀了羊,煮了粟米饭,还拿出了珍藏的果酒,招待商队的人。张远和昆莫坐在篝火旁,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从长安的集市,聊到西域的雪山,从丝绸的织法,聊到玉石的成色。阿吉木坐在旁边,认真地听着,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原不仅有高大的城池,还有热闹的集市,有能织出像云彩一样漂亮的丝绸的织机,有能写出像画一样好看的文字的书生。
张远还给他讲了汉朝的皇帝,讲汉朝的军队如何强大,如何在北方抵御匈奴的入侵。阿吉木听得入了迷,心里对那个遥远的中原王朝充满了好奇——他想知道,能建起那么高大城池的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也想知道,要是楼兰和汉朝交好,是不是就不用再怕匈奴人的骑兵了。
篝火渐渐小了下去,商队的人都回帐篷休息了。阿吉木跟着父亲回到议事帐,昆莫看着他兴奋的样子,笑着说:“今天听张首领说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中原很厉害?”
阿吉木用力点头:“是啊!他们有那么多好东西,还有那么厉害的军队。父亲,我们以后能不能和汉朝也交好,像和商队这样?”
昆莫点了点头,眼神变得深邃:“会的。但我们不能只靠别人,汉朝再强大,离我们太远了,真遇到危险,他们的军队赶不过来。只有我们自己建好了城,练出了能保护自己的力量,再和汉朝、和周边部落交好,楼兰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明天,你跟着商队的工匠好好学,把筑墙的法子记牢了,这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阿吉木重重地点了点头。他看着帐外的月光,月光洒在罗布泊的湖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银。他知道,明天会是新的一天,是楼兰人朝着“建城”这个目标,迈出的又一步。虽然他不知道这条路会有多难,不知道匈奴人会不会再来捣乱,不知道族人能不能一直团结下去,但他心里充满了信心——因为他有父亲,有巴图长老,有阿依娜,有整个楼兰部落的人,大家都在为了活下去、为了守护家园而努力。
他摸了摸肩膀上的疤痕,疤痕已经不疼了,却像一个印记,刻在他的身上,也刻在他的心里。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城池建起来,一定要让楼兰人再也不用害怕匈奴人的刀,一定要让罗布泊的水,永远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族人。
月光下,罗布泊的湖水静静流淌,胡杨林里传来几声夜鸟的啼鸣,营地的帐篷里,传来族人均匀的呼吸声。一切都那么安静,却又充满了力量,仿佛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希望——一个属于楼兰,属于这片沙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