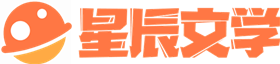万历七年四月廿一,江陵的日头已带着灼人的热气。徐光启站在汉江堤坝上,望着干裂的河床,眉头拧成了疙瘩。自三月以来,滴雨未下,原本该灌满春水的灌溉渠,如今只剩浅浅一汪泥水,沿岸的稻田裂开了指宽的口子,刚冒头的稻苗蔫头耷脑,像被抽走了精气神。
“先生,再不下雨,这一季的稻子怕是要完了。”王承祖蹲在渠边,用手挖了把土,粉末状的干土从指缝间簌簌往下掉,”军屯的’矮脚黄’虽然耐旱,可这半个月没水,也快撑不住了。”
徐光启顺着渠水望去,远处的闸门紧闭着,几个兵丁守在闸口,腰间的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他心里一沉——那是张家的私闸,去年张文明倒台后,张文昌仗着县里有人,硬是把公渠的闸门据为己有,说是”补偿张家被抄没的产业”。
“去看看。”徐光启带着赵勇往闸口走,刚靠近就被兵丁拦住。
“站住!张府的地界,不许靠近!”领头的兵丁横刀挡住去路,脸上带着倨傲——他是张文昌的家奴,仗着主子的势,连卫所的军户都不放在眼里。
“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徐光启亮出令牌,”这是官修水渠,什么时候成了张府的私产?”
兵丁瞥见令牌上的”巡视湖广”字样,气焰矮了半截,却仍强撑着:”是…是县太爷批的文书,让我家老爷代管闸口,说是…说是为了’合理分配水源’。”
“合理分配?”徐光启冷笑,”把水全引到你家老爷的稻田里,让百姓的庄稼枯死,这就是你们的’合理’?”他绕过兵丁,走到闸前——闸门只开了道缝,仅够张家庄园的稻田引水,下游的千亩民田却滴水未沾。
正在这时,几十个乡民扛着锄头赶来,为首的正是王家村的王二柱。”徐先生!您可得为俺们做主啊!”王二柱扑通跪在地上,身后的乡民们也跟着跪下,”张文昌把水全占了,俺们的稻苗都快干死了,再不放水,就只能去抢了!”
“都起来。”徐光启扶起王二柱,”抢解决不了问题。今天这水,必须放。”他对赵勇道,”把闸门打开。”
兵丁们还想阻拦,被军户们按住。赵勇抡起斧头,砸向闸上的铁锁,”哐当”一声,锈迹斑斑的铁锁落地,闸门缓缓升起,浑浊的渠水”哗哗”往下游涌去,像条欢腾的黄龙。
乡民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纷纷奔向自家的田埂,用锄头挖开田垄,让渠水顺着沟壑流淌。干裂的土地遇水,发出”滋滋”的声响,蔫了的稻苗仿佛瞬间挺直了腰杆。
徐光启站在闸边,看着水流过处泛起的绿意,心里却没多少轻松。他知道张文昌不会善罢甘休,这道闸门,不过是新的导火索。
果然,傍晚时分,张文昌带着周显谟和十几个家丁闯进布政司,指着徐光启的鼻子骂道:”好你个徐光启!竟敢强开我家闸口,我要去武昌府告你!”
周显谟在一旁帮腔:”徐先生,你擅自开启闸口,毁坏私人财产,于法不合啊。张老爷有县府的代管文书,你这样做,让下官很难办。”
“代管文书?”徐光启从卷宗里抽出份地图,拍在张文昌面前,”这是万历元年的水利图,明确标注此闸为’官闸’,供全县灌溉之用。你所谓的’代管’,不过是周知县徇私枉法的产物。”他转向周显谟,”周知县,不如咱们现在就去勘验——看看张府的稻田占了多少官渠水源,再算算百姓的损失,一并报给巡抚大人?”
周显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张文昌却梗着脖子:”就算是官闸,水源也该优先供应’有功之臣’!我兄长为朝廷效力时,你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兄长贪赃枉法被流放,你却靠着他的余孽侵占民利,这就是你说的’有功’?”李贽不知何时走了进来,手里拄着拐杖,声音虽轻却字字如刀,”老夫在姚安府时,也遇过抢水的乡绅,最后怎么着?被百姓捆起来扔进渠里,让他好好’尝尝’抢水的滋味。”
张文昌吓得后退一步,家丁们也缩着脖子不敢动。他们都知道李贽的脾气,看似温和,真动了怒,连巡抚都敢顶撞。
“张老爷要是觉得委屈,尽可以去告。”徐光启盯着他,”但在巡抚大人批复之前,这闸口得由军户看管,水源按田亩分配,谁也别想多占。”
张文昌气得浑身发抖,却找不出反驳的话,只能撂下句”走着瞧”,带着家丁悻悻离去。周显谟想跟出去,被李贽叫住:”周知县,明日把全县的水利文书都送到布政司,老夫要亲自核查——若是再查出私占官渠的事,你这个知县,也别当了。”
周显谟喏喏连声,几乎是逃着离开的。
夜里,徐光启在灯下翻看水利文书,发现江陵的大小水渠竟有三成被乡绅私占,有的甚至直接把渠水引到自家的池塘里,养鱼种藕,全然不顾下游的庄稼死活。
“这哪是争水,是争命啊。”李贽端着杯热茶走进来,”老夫年轻时在河南治水,见过为了半渠水打死人的,最后官府判’各打五十大板’,结果呢?水还是被有权有势的占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徐光启在地图上圈出被私占的水渠,”得重新制定水规,按田亩、人口分水源,再派军户和乡民共同看管闸口,谁也别想搞特殊。”
“谈何容易。”李贽叹了口气,”这些乡绅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动了他们的水,比动他们的银子还难受。”
徐光启却已拿定主意。他连夜写了《江陵水利疏》,详细列出私占水渠的弊端,提出”分田定水、军民共管”的方案,末尾写道:”水者,民生之本也。若任由豪强垄断,轻则饥馑,重则民变,伏望朝廷明察。”
第二天一早,他让人把疏文送报武昌府,同时带着军户和乡民代表,逐个勘验被私占的水渠。遇到不肯让水的乡绅,就拿出文书和地图,当众说理;遇到敢动粗的,就让军户出面制止。整整十日,竟真的把全县的水渠重新疏通,按新规分配水源。
通水那天,徐光启在汉江闸口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官渠民享,违者重罚”八个大字,落款是”万历七年,徐光启立”。乡民们敲锣打鼓,还在碑前摆了供品,说要让这块碑”镇住那些抢水的恶狼”。
徐光启站在碑前,看着渠水悠悠流淌,心里却清楚,这块石碑镇得住一时,镇不住长久。只要乡绅的势力还在,只要官场的贪腐未除,水渠里的纷争就永远不会停。
但他不后悔。就像这渠水,哪怕要绕过千道弯,撞碎万重阻碍,也总要奔向该去的地方——奔向那些嗷嗷待哺的稻田,奔向那些盼着收成的百姓心里。